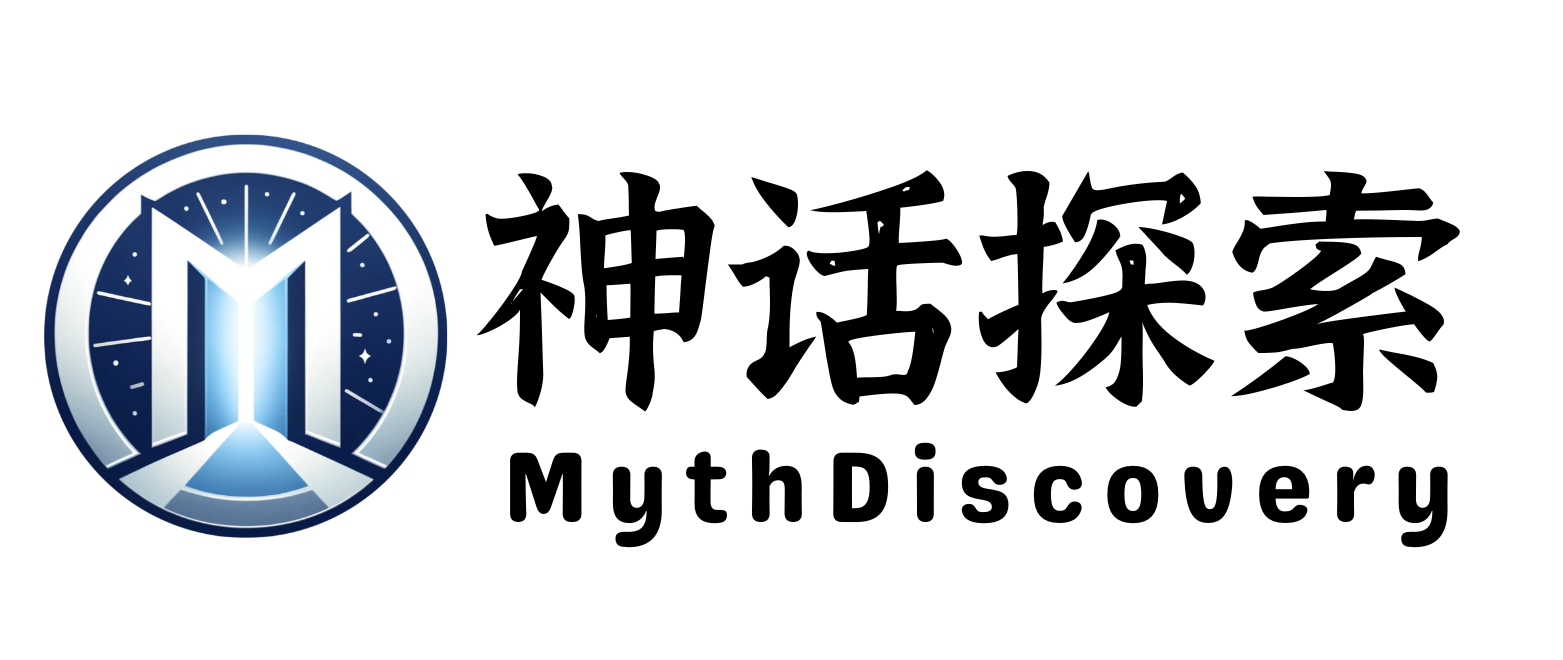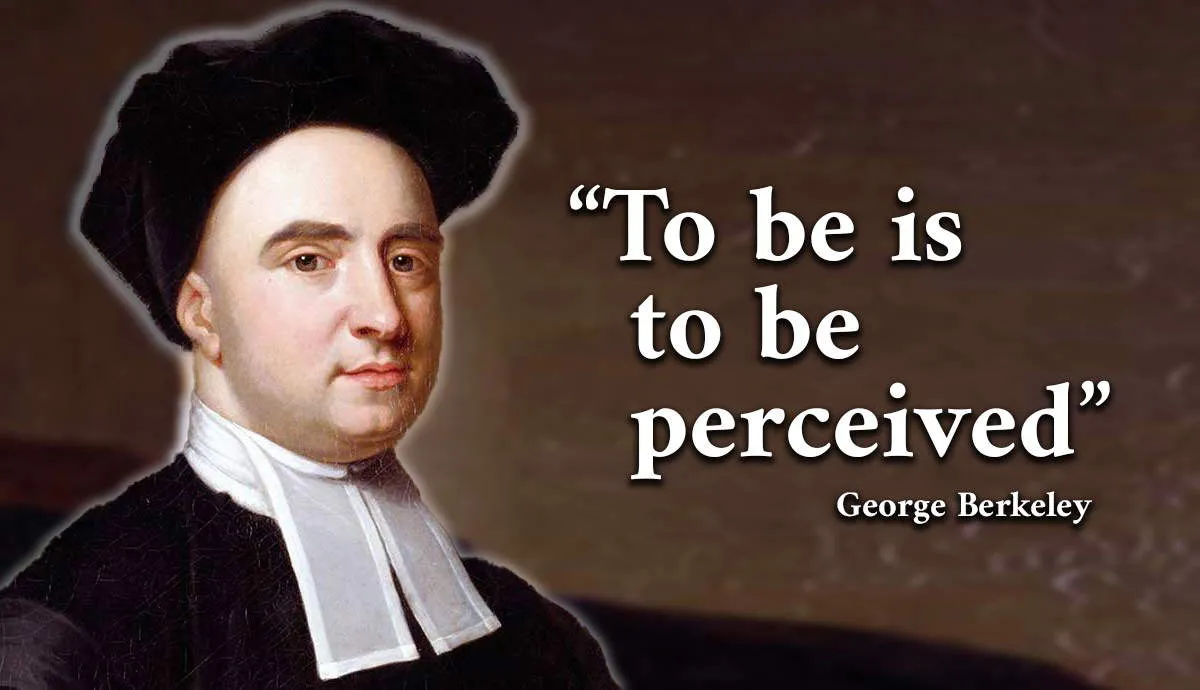解构——后现代主义先驱雅克·德里达的思想结晶——在当代哲学、文学批评和社会评论领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误解。表面上,它似乎旨在颠覆赋予艺术作品、文学文本和社会习俗的传统意义。然而,解构远比一些对其持批评态度的人所承认的要复杂和微妙。本文将介绍雅克·德里达的解构方法及其在解读文学文本中的应用。
解构与“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笼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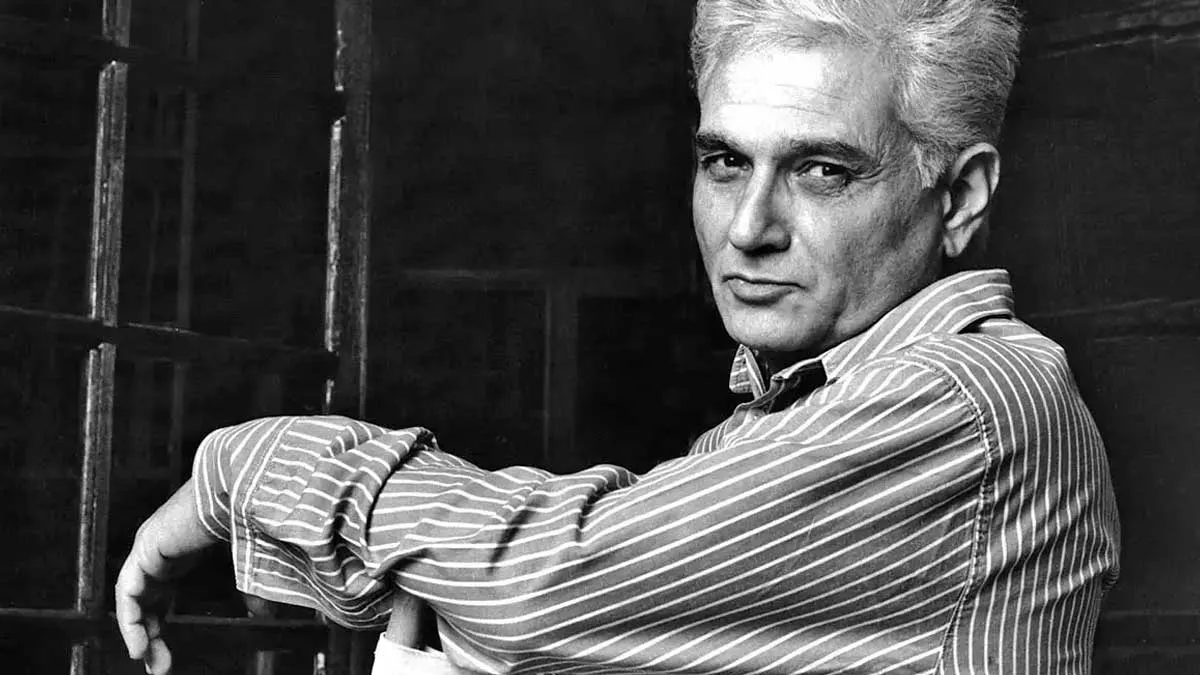 雅克·德里达的照片,乌尔夫·安德森拍摄。来源:德国广播文化
雅克·德里达的照片,乌尔夫·安德森拍摄。来源:德国广播文化
德里达提出的解构方法旨在揭示语言的绝对不确定性,它没有界限,是一个无限的意义游乐场。
在德里达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结构、符号与游戏》中,他将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描述为“逻格斯中心主义”。他用这个词来表达一个观点:纵观历史,形而上学总是假定存在一个“逻格斯”(意为“理性”或“语言”),它作为所有存在事物的中心。
各种理论都试图解释这个中心是什么,但它们都假定某种“在场”。在一些理论中,所有事物都只有一个统一的“在场”,例如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在其他理论中,则认为每一件个体事物都有自己的“在场”,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将“逻格斯中心主义”应用于语言意义的理论,它指的是任何声称词语与其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中心在场,赋予这种关系确定意义的理论。
为了进一步说明,逻格斯中心主义理论认为,某种基础在场使“雨伞”这个词与实际的物理雨伞之间存在着真实性。对于柏拉图来说,这可能是“雨伞性”的形式。对于当代分析哲学家来说,这可能类似于数学中的函数,其中输入可以生成“真”、“假”或“空”等输出。对于一些理论来说,它甚至被认为以上帝为中心!
结构主义:解构的反义词
 巴勃罗·毕加索的《吉他》,1913年。来源: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巴勃罗·毕加索的《吉他》,1913年。来源: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结构主义是德里达广泛探讨的关于意义的一种“逻格斯中心主义”理论。以下是他对结构主义的解释:
在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中,“固定起源”——德里达有时称之为“先验所指”——被认为是确定意义的来源。 “雨伞”这个词具有固定、确定的意义:它指的是实际的雨伞。根据结构主义,词语、物体和真理之间存在某种结构,赋予语言中的意义。因此,这个名称的由来!
然而,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人们意识到,这个中心或“固定起源”处于一个持续的链条中,一个中心取代另一个中心。当一个中心被证明是错误的,就会引入另一个中心。当这个新的中心不再闪耀动人时,裂缝便开始显现,一个新的中心就会成为潮流。
这种循环促使人们开始“认为没有中心,中心无法以在场存在的形式被思考”(280)。换句话说,那些注意到这种循环的人开始认为,存在的不是中心的在场,而是一种缺席。
解构作为游戏
 《缝纫机与雨伞》,萨尔瓦多·达利,1941年。来源:海德现代艺术博物馆
《缝纫机与雨伞》,萨尔瓦多·达利,1941年。来源:海德现代艺术博物馆
解构是对这种缺席和无限意义的完全接受,正如德里达所描述的,“对世界游戏快乐的肯定……对一个没有错误、没有真理、没有起源的符号世界 的肯定。”换句话说,解构是一种“游戏”!
将解构应用于文本时,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通过这种“游戏”变得明确。一个传统上被解释为表达“这个”的文本可以被解释为同时表达“不是这个”。这不仅仅是拒绝一种解释而支持另一种解释。它是在一个容器中同时找到词语的意义和词语的矛盾!
德里达写道,这是因为一个词语并不包含它的意义,就像以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它的意义是由德里达创造的延异——意义被推迟到使这个词与其他词不同的东西。
例如,“雨伞”这个词是由它与“洒水器”或“微波炉”等词语的无限差异链构成。更进一步,如果一个人沿着正确的线索走下去,可以在“雨伞”这个词中找到“不是鸭子”或“两足动物”的概念。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获得“雨伞”的意义,但我们会得到一个详尽的列表,列出它不是的所有东西。这就是德里达感兴趣的意义的“推迟”。
因此,根据德里达的说法,一个词语的意义存在于推迟到它的差异的无限链条中。当这个链条最终回溯到它的反义词时,兴奋就开始了。因此,解构的解读是一种方法,它通过延异的“游戏”表明所有文本在其自身内部都包含矛盾的意义。例如,“满”这个词一旦被解构,就同时包含了“已满”和“空”的概念——反义词和矛盾。
这种将事物拆开,沿着链条的链接追溯到内在矛盾的过程,就是解构的含义。这个过程是一种游戏;我们不必为意义的丧失而悲伤,而是可以为最终从确定性和僵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欢欣鼓舞!
解构文学文本的例子
 《吞噬其子的土星》,弗朗西斯科·戈雅,1820-23年。来源: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吞噬其子的土星》,弗朗西斯科·戈雅,1820-23年。来源: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解构,看看它在实际应用中的例子会有所帮助。为了简洁起见,我选择了一首短诗——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设计》——并尝试展示如何将解构作为一种方法应用。
这首诗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对存在设计者的上帝的宇宙论证的一种颠覆。因此,解构的解释将表明,这首诗也包含一个相反的结论。
传统的解释
 一种天然的夏枯草的照片,N. Baudet拍摄,2012年。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一种天然的夏枯草的照片,N. Baudet拍摄,2012年。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这首诗由两节组成。第一节描述了叙述者遇到的景象:
这个场景从一开始就显得平淡无奇。我也遇到过身体饱满的白色蜘蛛,并没有感到不安。那些腹部有红色斑点的黑色蜘蛛才是需要警惕的对象,对吧?
错了!这只特殊的蜘蛛栖息在一朵白色的夏枯草上,爪中抓着一只白色的飞蛾尸体。夏枯草是一种花,通常是蓝色的。然而,这朵夏枯草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白色。这就是为什么叙述者对这个场景感到不安——三个纯白色的元素如此不可思议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蜘蛛能够捕获并吞噬飞蛾。
弗罗斯特将这三样东西称为“女巫魔药的成分”,因为它们似乎是故意被选中来制作邪恶的女巫魔药。
这使我们进入这首诗的第二节。我们的叙述者被眼前所见感到不安,开始思考一系列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天然的蓝色花朵变成了不自然的白色?此外,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只白色的蜘蛛和这朵白色的花朵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最后,是什么——或者是谁——要为引导这只可怜的白色飞蛾走向其他两个,最终走向死亡负责?
弗罗斯特在这节诗的最后两行给了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这种情况是按照设计而发生的话,那就暗示着存在设计者。或者,如果这三样白色事物确实是“女巫魔药”的成分,那么一定有一个主厨精心策划了这个食谱。令人毛骨悚然的转折是,如果在这个黑暗的场景中存在着设计者——或主厨——那么他一定是邪恶的。
换句话说,这首十四行诗是对邪恶之神存在的宇宙论证。只有邪恶之神才会设计出白色蜘蛛、变异的花朵之间这种几乎不可能的组合,然后故意引导不幸的飞蛾直接飞向它们。无论如何,宇宙并不是一个友好的地方。我们任由邪恶的主厨摆布。
发现内在的矛盾
 《阿拉克涅》,奥托·亨利·巴赫,1884年。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阿拉克涅》,奥托·亨利·巴赫,1884年。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如果从这首十四行诗中我们只能获得一个明确的解释,那就是这三个死亡角色都是白色的。弗罗斯特告诉我们,蜘蛛、飞蛾和夏枯草都是单独的,也是总体的白色。
然而,我们也被告知蜘蛛、飞蛾和夏枯草是“死亡和厄运的各种角色”。
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厄运”这个词。具体来说,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由真菌或霉菌引起的植物疾病。植物可能会出现厄运。另一个“厄运”的含义是城市中一些变得破败不堪、无人照管的区域。城市可能会出现厄运。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一种破坏性的状况,会阻止事物的健康生长。
这里我们可以讨论为什么“厄运”这个词在这首诗中如此有趣。它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古挪威语的blikna,意思是“变淡”。
我们的白色要素感染了“厄运”,这个词包含了古挪威语含义的痕迹——这意味着我们的白色角色正在变淡或变成白色。
但是等等,如果蜘蛛、飞蛾和夏枯草正在变成白色,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它们不是完全白色的。相反,它们有颜色,正在失去颜色。
因此,尽管我们五次被告知我们的要素的白色,但我们也被告知它们根本不是白色的!蜘蛛、飞蛾和夏枯草既是白色的,又不是白色的,这可以通过“白色”和“厄运”这两个词体现出来。对设计者进行推断是基于白色蜘蛛、飞蛾和花朵之间几乎不可能的组合。如果没有这三样东西,就无法对设计的宇宙或设计者上帝进行推断。
重新审视这个场景,考虑到我们新解构的“厄运”,对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不再具有说服力。总之,解构认为,这首诗确实对上帝进行了宇宙论证,但又没有对上帝进行宇宙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