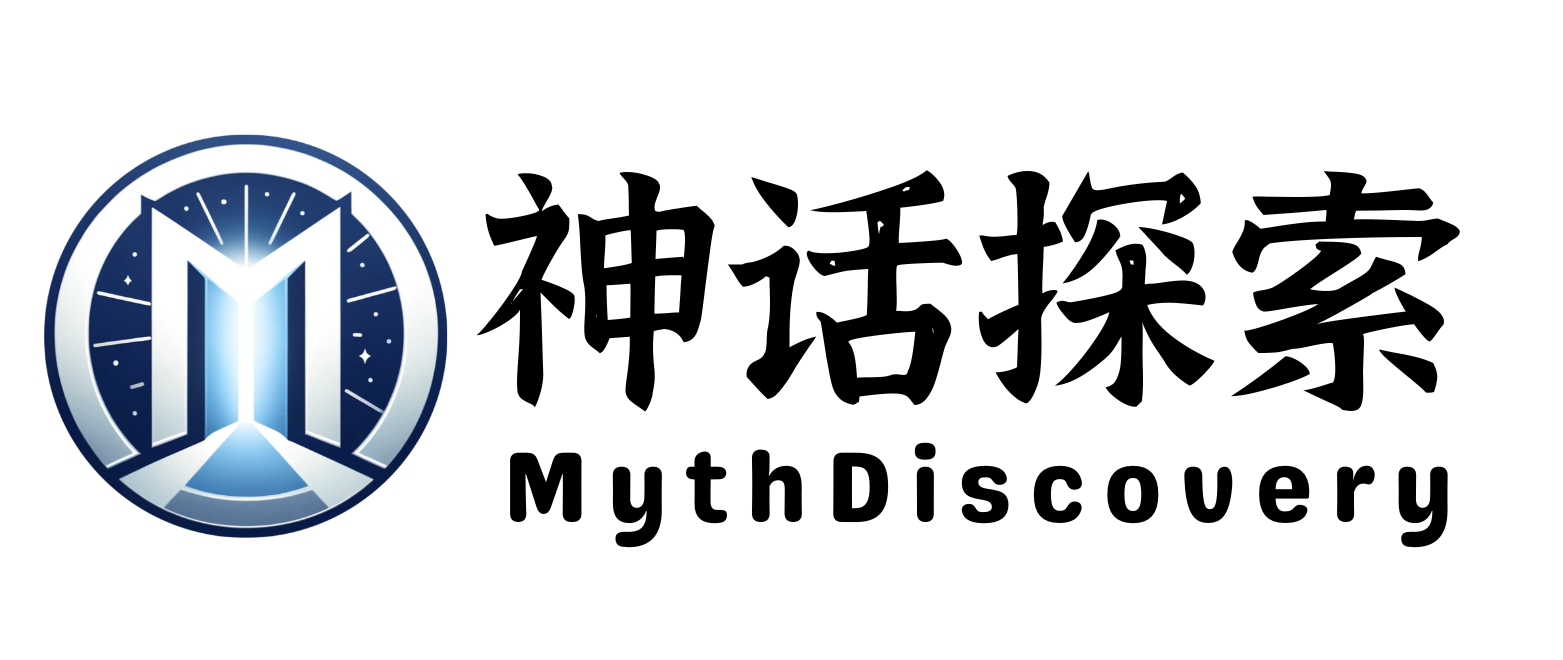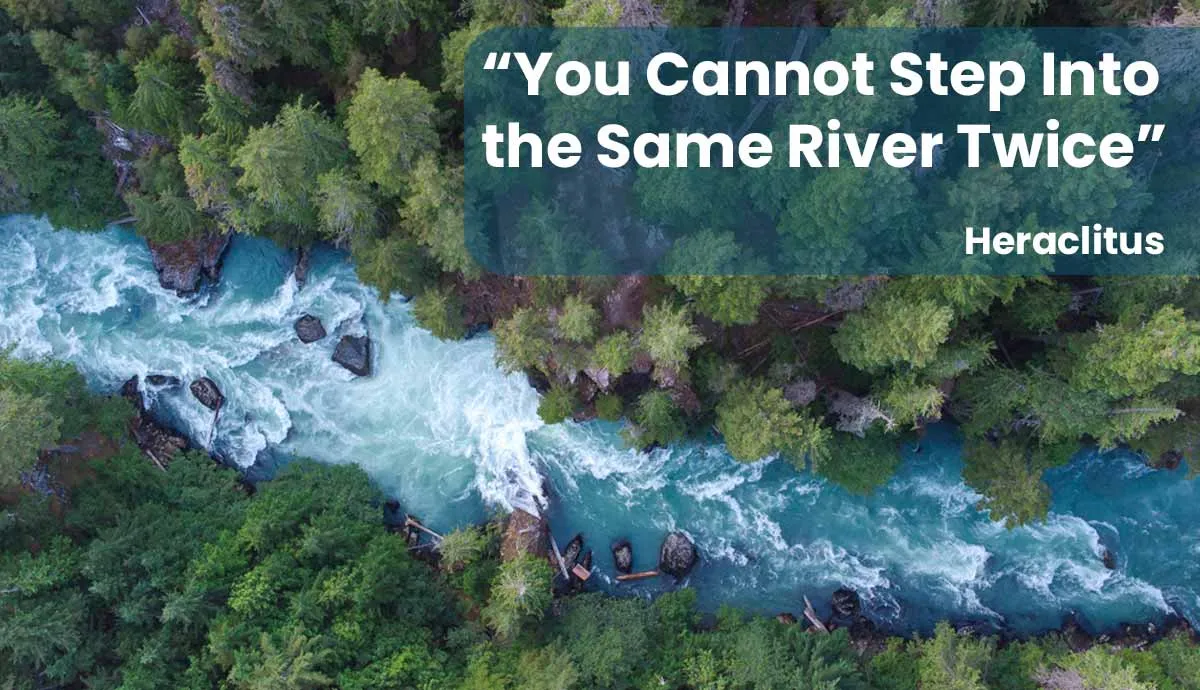人类凭借其非凡的理性、分析和自我反省能力,站在了动物界顶峰,可以像其他物种一样操控和控制周围环境。然而,这种非凡的进化礼物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挪威哲学家彼得·韦塞尔·扎普菲认为,智力既是人类最大的礼物,也是最危险的诅咒。
人类进化悲剧是什么?

人类进化的悲剧在于,人类渴望在一个本质上毫无意义的宇宙中找到意义。智力是我们进化的苦乐参半的果实。凭借着对因果关系的出色排序,智力开始在无处可寻之处寻找原因。与其他任何动物不同,人类是唯一一种拥有自然无法满足的基本需求的物种——对生命的终极意义和目标。扎普菲用优美的散文将智力比作一把双刃剑。人类利用其锐利的认知能力,可以在世界上劈开任何东西。
然而,扎普菲警告说,无论是谁使用这把刀,都必须“将其中的一面转向自己”(扎普菲,1933)。意识的两面,即外在和内在,在矛盾中服务于我们。当面对外部世界时,我们意识的认知能力使我们站在食物链的顶端。然而,当面对我们的内心世界时,它却摧毁了我们。

自然背叛了人类。通过过度发展单一能力,人类变得不适合生存,无法承受自我意识的重担及其内心生活的危险。扎普菲认为,这种背叛在于,自然“创造了奇迹,却拒绝承认他的存在”,拒绝为他内心对意义的渴望提供答案(扎普菲,1933)。扎普菲用亚当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来解读这种人类状况的悖论,其中生命树象征着受诅咒的自我意识的礼物。
我们“过剩的意识”使我们成为“宇宙无助的囚徒”——意识到自己的短暂性,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毫无意义,却对此无能为力(扎普菲,1933)。扎普菲在《最后的弥赛亚》这部巨著的核心问题是,大多数人如何才能在他们存在现实的令人心碎的焦虑中生存下来。
我们如何才能在毫无意义的存在中生存?

我们通过人为地麻木自己的意识来生存,如果我们病症的诊断是意识过剩,那么治疗方法肯定在于抑制意识。扎普菲认为,“人类的生存是通过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抑制其危险的过剩意识来实现的”,这种抑制“成为社会适应的条件,以及人们通常所说的‘健康’和‘正常’行为的条件”(扎普菲,1933)。抑郁、焦虑或精神错乱只是对生命更深层现实的真实感知的副作用。这不是一种心灵的疾病,而是我们用来保护自己免受体验我们存在的短暂性和毫无意义的本性的恐怖的防御机制的失败。
扎普菲确定了四种主要的防御机制,它们构成了我们抑制过剩意识的无数方式:隔离、升华、依恋和转移。隔离是我们倾向于互相隐瞒我们存在状况的倾向。它是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协议,旨在掩盖和审查我们对生命真实本性的认识。升华是一种以转化而非抑制为特征的防御机制。通过升华,我们从生活的悲剧中抽离出来,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它们,欣赏它们的审美价值。艺术家将痛苦转化为诗歌、绘画、电影或小说就是这种情况。最后两种防御机制,依恋和转移,是我们抵御存在虚无的恐怖的最强大的堡垒。
依恋和转移如何拯救我们?

依恋和转移通过将我们意识的注意力从我们的短暂性以及我们存在的毫无意义的现实中转移开来,从而拯救了我们。扎普菲将依恋定义为“试图在意识的不断变化的混乱中建立固定点,或围绕它建立一道墙”(扎普菲,1933)。依恋从童年早期就开始形成,那时我们视自己的生活特征(例如父母、朋友、日常事务等)为理所当然。我们享受着一种虚幻的安全感,直到我们意识到这些依恋与其他事物一样短暂和偶然。然后我们就会更换它们,这个循环不断重复。依恋既是个人性的,也是集体的。
扎普菲认为,“每一个社会单元都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的依恋系统,建立在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的坚固基础上”(扎普菲,1933)。这些依恋系统是社会规范的根源,通过社会政治甚至宗教的奖惩机制得到保护。最终,个人和集体依恋形成的矩阵纯粹是虚构的。

另一个主要的堡垒是转移。转移通过“不断地用新的印象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的意识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Zappfre,1933)。与依恋不同,转移策略通常是有意识的行为。我们害怕无所事事,没有东西可以转移我们对自我的注意力。我们不是逃离无聊,而是逃离潜藏在我们注意力表层之下令人毛骨悚然的深渊。我们经济的基石是为了帮助我们从“我们来自虚无,也走向虚无,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这一事实中分散注意力(扎普菲,1990)。
其他一切都是这四种防御机制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的结合。例如,我们对物质财富和权力的渴望与它们的直接实际用途无关。本质上,“拥有巨大财富的真正价值在于,富人可以支配各种各样的潜在依恋或消遣”。反过来说,这就是为什么监禁是一种惩罚。
彼得·韦塞尔·扎普菲是一个幽默而悲观的悲观主义者,他在论文的结尾没有给我们任何希望。他为摆脱我们存在状况的痛苦而提供的唯一建议是简单地停止生育。在他最后一部主要作品中,他俏皮地告诉他绝望的读者:“不幸的是,我帮不了你。我面对死亡的唯一办法,就是愚蠢的微笑”(扎普菲,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