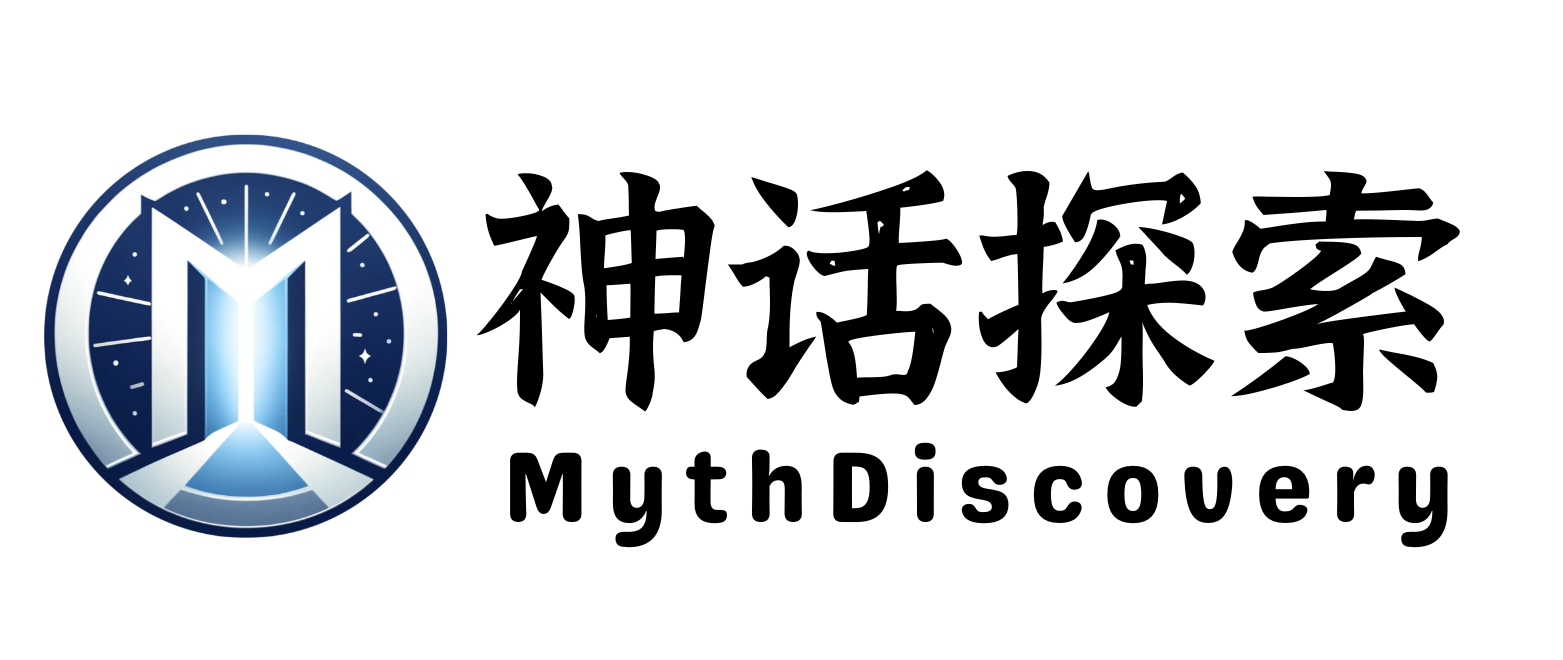几个世纪以来,刺绣一直被视为一种以女性为主的装饰性手工艺,承载着丰富的象征和宗教意义,却从未被提升至“严肃艺术”的殿堂。直到20世纪,这一观念才开始发生转变,女性艺术家们积极拥抱刺绣作为一种表达抗议和身份认同的媒介。让我们深入探究刺绣在艺术史上源远流长的故事。
刺绣的起源与深层含义

中国16-17世纪的丝绸刺绣龙纹椅条。来源: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作为一种实践,刺绣在人类学会将两块兽皮缝合在一起后不久便应运而生。然而,人们将其用于装饰目的,则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尽管风格、主题和所用材料各异,刺绣作为一项技艺几乎存在于全球大多数文化之中。在中国,一些现存最早的刺绣作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至3世纪,展现了其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工艺。
精美复杂的刺绣,尤其是那些使用金线或银线制作的作品,曾是财富和地位的显著标志。例如,那些在特定文化中创作出的卓越刺绣服饰或配饰,作为备受推崇的艺术珍品,曾远播世界各地,成为令人垂涎的收藏品。刺绣本身就是一种奢华的元素,其制作耗费了数小时乃至数十小时的艰辛劳动,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权力和影响力的象征。在基督教文化中,刺绣也被广泛用于创作宗教图像和装饰教堂,以精湛的技艺来表达绣工们对上帝的虔诚信仰。

19世纪晚期的罗马尼亚刺绣衬衫。来源: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传统刺绣往往兼具仪式性和保护性功能。特别是在东欧地区,刺绣服饰被视作护身符,能够保护佩戴者免受邪眼或厄运的侵扰。刺绣布料和毛巾在婚礼、葬礼,以及将新生儿介绍给家庭的仪式中曾被(偶尔至今仍被)广泛使用。最初,这类刺绣上的每一个元素都承载着特定的含义,然而,很遗憾,大部分解释性资料并未流传至今。有些刺绣作品甚至能够讲述完整的故事,内容涵盖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或是对于创造其文化的民族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
文艺复兴时期,富有的意大利人委托制作刺绣挂毯和大型作品来装饰他们的宅邸。这项手工艺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以至于许多著名艺术家,如拉斐尔,都曾亲自创作刺绣设计图稿,足见其在当时艺术界的影响力。
“女性专属”的工艺

约1788年,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刺绣的壁炉屏风。来源: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刺绣主要被归类为一种“女性专属”的工艺。当男人们忙于处理外部世界的事务时,女人们则在家中漫长的夜晚里专注于这项精细的劳作。即使是地位最高的女性,例如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学习并练习刺绣。擅长刺绣被认为是嫁入豪门的一项宝贵资本,这不仅仅因为其本身是一项精湛的技能:刺绣需要耐心和专注力,并且占据了女性大量的时间,从而使她们变得温顺和安静。正因如此,现代的女权主义艺术家们常常拒绝使用这种媒介,将其视为与父权制有着内在联系的象征。
刺绣实践中这种性别化的属性,对其保存和研究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由于被贬低为一种家庭爱好,对其进行的罕见研究往往是民族志式的而非艺术史式的,因此,大量关于刺绣的知识、信仰和深刻含义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无闻,令人惋惜。
手工艺的复兴

忍冬花刺绣,由威廉·莫里斯设计,简·莫里斯刺绣,19世纪80年代。来源:威廉·莫里斯画廊
在19世纪末之前,刺绣一直作为一种居家装饰性实践而静静地存在着。直到一群艺术家,对工业革命的负面影响深感不安,开始将目光转向那些此前被视作“纯粹手工艺品”的媒介。由著名设计师威廉·莫里斯领导的工艺美术运动,强调了生产过程的统一性以及对手工劳动的重视。为此,他们致力于复兴传统的装饰性手工艺,并将其融入日常物品和家具设计之中。刺绣在这次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威廉·莫里斯甚至出版了带有刺绣图样的书籍,极大地推广了这项技艺。
几十年后,在法国,一群艺术家着手解构传统的艺术等级制度。这个团体自称为“纳比派”(Les Nabis,源自希伯来语“先知”的错误音译),呼吁开启一个艺术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各种形式和媒介都应被平等对待。该团体由皮埃尔·博纳尔和莫里斯·德尼等著名艺术家组成,他们深受日本艺术和各种东方文化的启发。该团体的核心成员均为男性,但他们经常与家族中的女性合作:保罗·朗松的妻子根据他的画作创作刺绣,而雕塑家乔治·拉孔布的母亲则编织了充满神秘符号的挂毯,共同探索艺术的无限可能。
精神病院患者与刺绣

洛丽娜·布尔沃的挂毯作品。来源:残障艺术在线
随着精神病学的发展,刺绣实践突然获得了广泛关注。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医生们开始关注精神病院患者作为康复项目一部分所创作的艺术品。那些病情稳定到可以工作的患者,经常被强制安排在工厂里缝制衣物。许多女性,通常在被亲属遗弃后被送入精神病院,通过她们的作品表达了内心的沮丧和恐惧。
这类患者中最著名的一位名叫洛丽娜·布尔沃(Lorina Bulwer),她曾是一名裁缝。布尔沃在父母去世后被送入一个习艺所,她的兄弟甚至付钱给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让她一直留在那里。布尔沃内心充满沮丧和愤怒,她通过精细的刺绣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所有文字都用大写字母书写,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其中就包含了那句悲惨的感叹:“我在这该死的炼狱里浪费了十年生命”(I HAVE WASTED TEN YEARS IN THIS DAMNATION HELL FIRE)。除了表达她的痛苦,布尔沃还通过缝制人物和物体并添加文字,创作出了一整套漫画书般的连环故事。她通过这些作品讲述的一些故事,使得今天的研究人员怀疑她在被囚禁期间可能遭受了性虐待。

阿格尼斯·里希特刺绣的夹克。来源:The Vale Magazine
另一位因在精神病院创作刺绣而闻名的女性是阿格尼斯·里希特(Agnes Richter)。里希特是一位近五十岁的德国女性,因被怀疑患有偏执症而被送入医院。在她25年的隔离生活中,她制作了自己的衣服,并在上面绣上简短的短语来描述她的生活。最突出的图案是数字583,她用它来标记她的洗衣物品,以及记录记忆或随意的想法。不幸的是,在她数量庞大的作品中,据说只有一件夹克幸存了下来。对里希特或布尔沃这类自学成才艺术家的作品的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局外人艺术”(Outsider Art)的兴起而达到顶峰。
朱迪·芝加哥的《晚宴》

朱迪·芝加哥的《晚宴》,1979年。来源:Britannica
20世纪最著名的将刺绣融入其中的艺术作品之一,便是朱迪·芝加哥的《晚宴》(The Dinner Party)。这项大型装置艺术旨在向西方历史上重要的女性致敬,同时也是对包括刺绣和花卉绘画在内的“女性”艺术和手工艺的颂扬。芝加哥呈现了一张为39位女性设置的三角形餐桌。每个座位都绣着一位女性的名字,配有一套玻璃杯和一个独特的陶瓷阴户形状花卉构图的盘子,每个盘子都为各自的女性定制。三角形的每边有13个座位,以此影射《圣经》中只有男性出席的“最后的晚餐”。整个装置作品融合了各种传统上归属于女性的手工艺,并以一种宏伟且带有仪式感的方式呈现出来,挑战了传统艺术史的叙事。
在她其他的项目中,朱迪·芝加哥也同样运用刺绣作为一种女权主义媒介,借此引入艺术史以往所忽视的主题。尤其是她编织和刺绣的系列作品《诞生计划》(The Birth Project),恭敬地叙述了分娩的过程,将这一原本被艺术界视为禁忌的主题,转变为一场神圣的仪式,赋予其深刻的意义和尊严。
当代艺术中的刺绣

弗里达·托兰佐·耶格尔的《愤怒是无意义时代的一台机器》,2024年。来源:Bortolami Art Gallery
如今,刺绣已成为当代艺术中最受欢迎的实践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不断转变的内涵。女性艺术家们不再将其贬低为一种父权制的工艺,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与数百万前辈女性共同分享的实践而积极拥抱。这项实践的创造性和精神潜力被重新唤醒,并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宣言,常常用于抗议不平等和压迫。此外,就创作一件刺绣作品所需的劳动量而言,这种媒介也与几十年来主导市场的、相对迅速(或至少看似迅速)的姿态抽象艺术实践形成了鲜明对比,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

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乌兹别克斯坦馆。来源:Les Nouveaux Riches Magazine
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尤其重视那些在与原住民艺术实践相关或直接源于原住民艺术实践领域工作的艺术家。许多这类艺术家都以织物和刺绣为媒介进行创作,有时还会将其与其他媒介和影响力相结合。例如,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托兰佐·耶格尔(Frieda Toranzo Jaeger)呈现了一件大型装置作品,将墨西哥壁画艺术的典型绘画风格与散布在作品周围的小型刺绣融为一体。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馆则展示了传统的苏扎尼(Suzani)刺绣,并将其与AI生成的图像并置,揭示了技术中存在的文化偏见和刻板印象思维,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