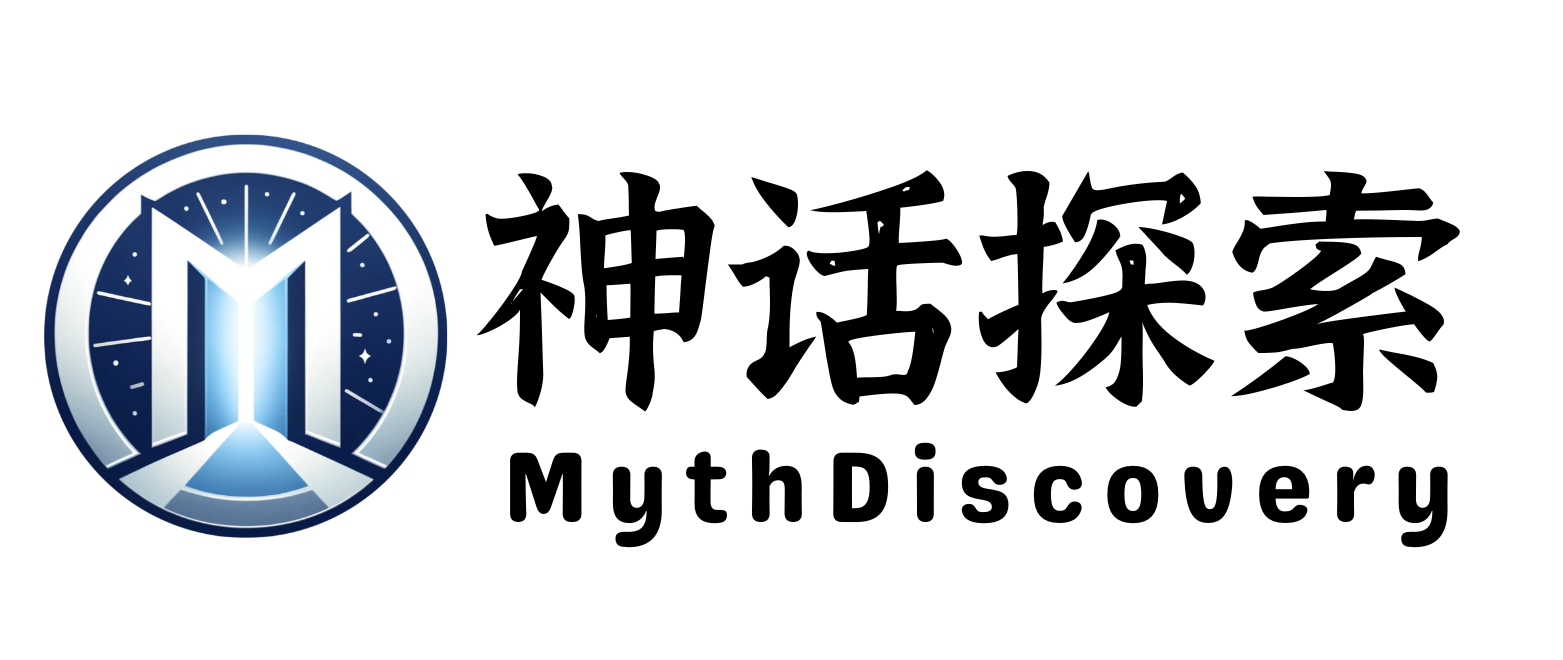“`html

弗洛伊德认为,“恐怖感”并非仅仅源于陌生和疏离感。诡异的事物,例如活娃娃、断肢和替身,都可能引发这种感觉。因为它们与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情感——交织着快感与痛苦——有关,这些情感一旦浮出水面,便会令人不安。弗洛伊德的观点对当时正探索抽象表现的视觉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为超现实主义运动注入了精神分析的动力。
弗洛伊德与现代艺术:梦境与潜意识

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都以其对梦境的关注而闻名。弗洛伊德在1919年创作《恐怖谷》时,他的《梦的解析》(1899) 已经出版。这篇文章融合了他的理论:梦境揭示了我们被压抑的欲望和恐惧,尽管往往以难以捉摸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梦境常常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呈现出“本应隐藏…的秘密…却变得可见”的事物,正如他本人对恐怖谷的定义。这些事物呈现出既熟悉又陌生的独特气质。

这种混合是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完美比喻,它运作于熟悉(经常将目光投向平庸的日常物品)与陌生、难以理解和梦境般的元素的交汇点。达利的《蜂鸟引起的一场梦》(1944年)是最明显的例子,它是一幅受梦境启发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充满了具有潜在象征意义的物体。

形而上学绘画运动(与超现实主义一样,其名称由诗人阿波利奈尔命名)在描绘梦境的恐怖谷方面走得更远。弗洛伊德所说的我们在梦中“有时会经历的无助感”,源于与被压抑的事物对抗,这在基里科和坦吉的绘画中显而易见。
基里科看似毫不相关的物体的组合、他作品中长长的阴影以及他以细致的几何细节在较小的画布上描绘的荒凉城市,都唤起了梦境般景观的同时虚幻与真实感。坦吉更为稀疏的风景中,常常点缀着抽象的形状,像是真实物体的奇异阴影。

莱奥诺拉·卡林顿虽然不像许多超现实主义的男性拥护者那样完全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但她创作的诡异作品将普通的物体和环境与非凡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营造出类似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类型的效果。

多萝西娅·塔宁也采用了普通空间,如客厅、酒店房间和走廊,并赋予它们一种令人不安的氛围。
替身或双重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也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替身——双重、倒影、影子或孪生——可能是恐怖谷的体现。遇到一个与自己惊人相似的版本可能会引起“所有未实现但可能实现的未来,我们仍然喜欢在幻想中依恋这些未来,所有被不利的外部环境压垮的自我努力”,同时它也可能提醒我们自己的死亡。双重性动摇了我们对存在的感知,难以辨别自我从何开始,到何结束。
马格里特的画作中常常出现双重形象:从《魔术姿态》(马格里特后来将其切成碎片并重新绘画)到《双重秘密》(其中脸部本身在其复制品中变得支离破碎),两者都在1927年创作。1937年的《复制禁止》和1955年的《地平线的奥秘》也描绘了从略微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复制人物。

雷梅迪奥斯·巴罗的梦境景观,与卡林顿的作品一样,展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其中常常出现诡异的人物。这些中性性别的人物不仅在巴罗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在同一幅画布上也会出现,就像1956年的《杂耍演员》一样,营造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混乱感,难以辨认区分不同的人。

弗洛伊德的恐怖谷理论不仅影响了超现实主义绘画。克劳德·卡洪在多张自画像摄影作品中都融入了镜像和双重意象,包括《你想要我做什么?》(1929)。卡洪的作品体现了弗洛伊德对双重形象的吸引和排斥:另一个自我既是未来的可能性,也是对自身稳定性的威胁,这对于这位不符合性别规范的艺术家来说,有着特殊的共鸣。
娃娃和肢解

《恐怖谷》的一部分关注一个名为《沙人》的短篇故事,该故事于1817年由E.T.A.霍夫曼发表,弗洛伊德称其为“营造恐怖谷氛围的无与伦比的大师”。弗洛伊德对这个故事的解读集中在主角害怕沙人挖掉他眼睛背后的阉割情结,但这个故事还包含另一个可以归类为恐怖谷的元素:一个令人不安地逼真的木制娃娃奥林匹亚。
娃娃、人体模型、木偶和自动机可能会扰乱我们区分虚构与现实的能力,重新点燃我们婴儿时期的幻想,认为我们玩的玩具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无法立即分辨它们的活动方式,这些东西就会变得尤其诡异。出于同样的原因,再加上阉割情结的心理分析层面,看到似乎保留了一些生命迹象的肢解的身体部位,我们会感到毛骨悚然。
在探索娃娃和肢解的恐怖谷方面,德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汉斯·贝尔默是无与伦比的大师。显然,受雅克·奥芬巴赫的《霍夫曼的故事》(该剧为舞台改编了《沙人》)的演出影响,贝尔默于1933年制作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年轻女孩的娃娃,他不断地拆卸和重新组装娃娃的各个部位,然后在各种场景和位置拍摄。这组作品于1934年出版为《玩偶》,由于它迫使观众重新调整他们对彻底解构的女性身体的物化凝视,引起了巴黎主要超现实主义者如安德烈·布勒东的注意。

其他使用新技术将身体部位移植到陌生新环境中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师包括克劳德·卡洪和多拉·玛尔。卡洪的《我伸出双臂》(1931/1932) 显示出一对手臂似乎从墙内伸出。玛尔,作为毕加索许多绘画作品中的模特,也在摄影领域创作了创新作品,包括1934年的《无题(手壳)》。正如标题所示,它描绘了一只人手似乎从贝壳中长出来。

最近的摄影师们利用了他们媒介中诡异的可能性,这从本质上扰乱了我们对每一刻短暂性的感知,保存了似乎属于过去的时刻和人物。1999年,杉本博司开始了一个名为《肖像》的系列,描绘了著名历史人物的蜡像,通过相机将其转化成活生生的样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辛迪·舍曼拍摄的照片将人物形象(通常是舍曼本人)变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类似于真实人物的形象。在她名为《无题》的系列中,编号345只是她众多照片中的一张,在这张照片中,舍曼效仿贝尔默,分解并以怪异的方式重新组装了一个女性玩偶的身体部位。
现代艺术与令人不安的现实

恐怖谷很难定义,弗洛伊德最初的论文大部分都致力于描述恐怖谷并非是什么。但对于超现实主义者和后来的艺术家来说,它代表了任何现实被扰乱的景象,无论是通过不真实、梦境、魔法的元素,还是通过超现实:对真实、熟悉和家常事物的夸大或过度关注,揭示了其下潜在的焦虑和压抑。
马格里特的《拿着报纸的人》(1928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利用看似普通的事物来引发观众的不安。它的四个画面展现了一个平淡无奇的室内场景,最初看起来的区别只在于标题中的人物和他的报纸出现在第一个场景中,而其他三个场景中没有。然而,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他三个场景之间存在细微的视角差异,观众会对该男子消失的情况以及马格里特将这四个画面像连环画或“找不同”游戏一样呈现出来的原因产生一种诡异的困惑。

在玛尔的《模拟器》(1936年) 等照片中,看似无辜的空间呈现出一种不安的边缘,照片中展示了一个男孩在一个某种密室中,他的身体扭曲着,处于狂喜或痛苦之中。舍曼的照片经常通过其怀旧感来唤起恐怖谷,提醒观众摄影的奇特能力——让久已消失的事物似乎依然存在。她所谓的“厌恶”系列中的照片将食物、药品和化妆品等普通物品变成了腐烂和解体的象征。
最后,恐怖谷在戴维·林奇的作品中走向了荧幕。他的电视剧集《双峰》(1990-91, 2017) 的背景设定在一个普通的美国小镇,某种不明邪灵的存在更加令人不安,因为它潜伏在如此普通的环境中。林奇创造了经久不衰的诡异和超现实主义的视觉效果,使用了树木、猫头鹰、原木、替身(女演员谢丽尔·李扮演劳拉·帕尔默和她的表妹麦迪·弗格森)和梦境般的景观,如神秘的红色房间等主题。

瞬间就能认出的红色房间既熟悉又陌生。它配备了沙发和灯具,装饰着让人想起基里科画作的维纳斯雕塑,然而,它却是一个人们倒着说话并变成自己替身的地方。像所有恐怖谷最好的例子一样,它并非彻头彻尾地险恶,而是利用了我们的潜意识,以同样的方式吸引和困扰着我们。
参考文献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 (1919). 《恐怖谷》, 阿利克斯·斯特拉奇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