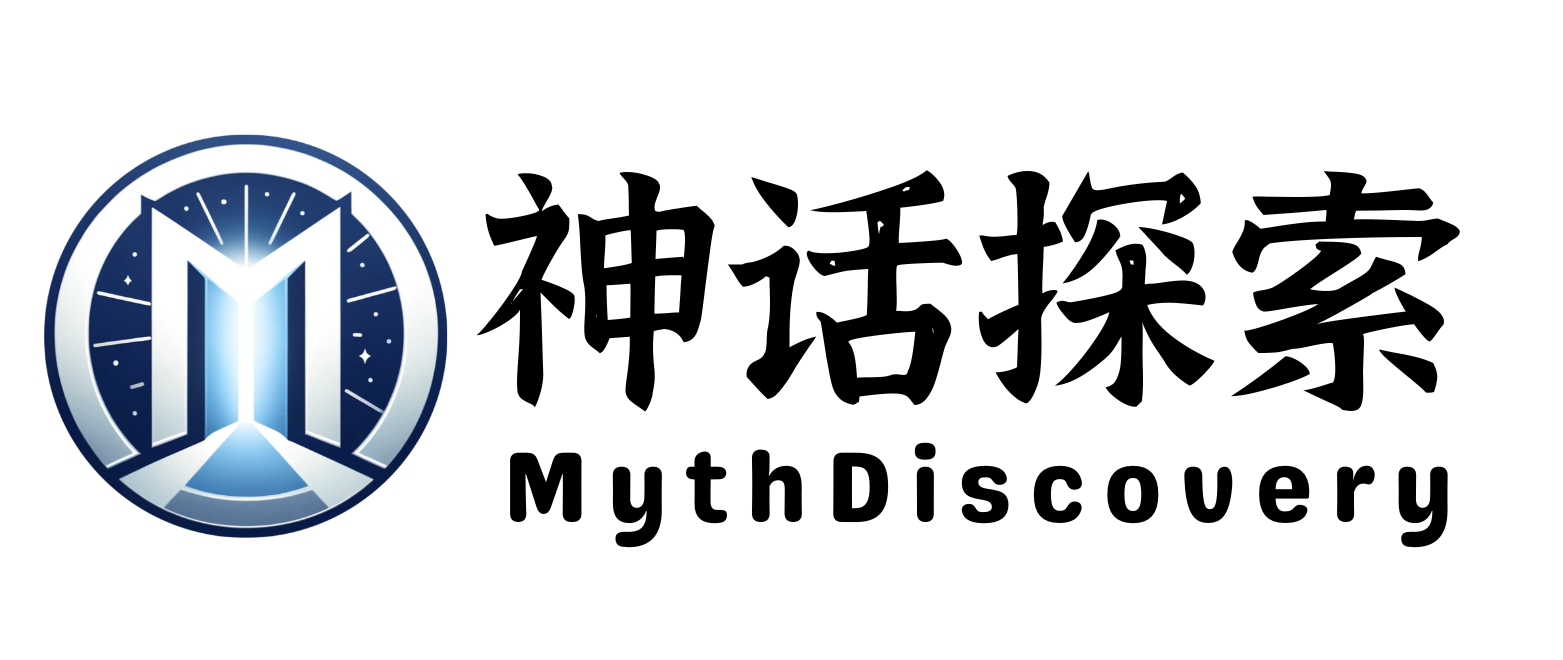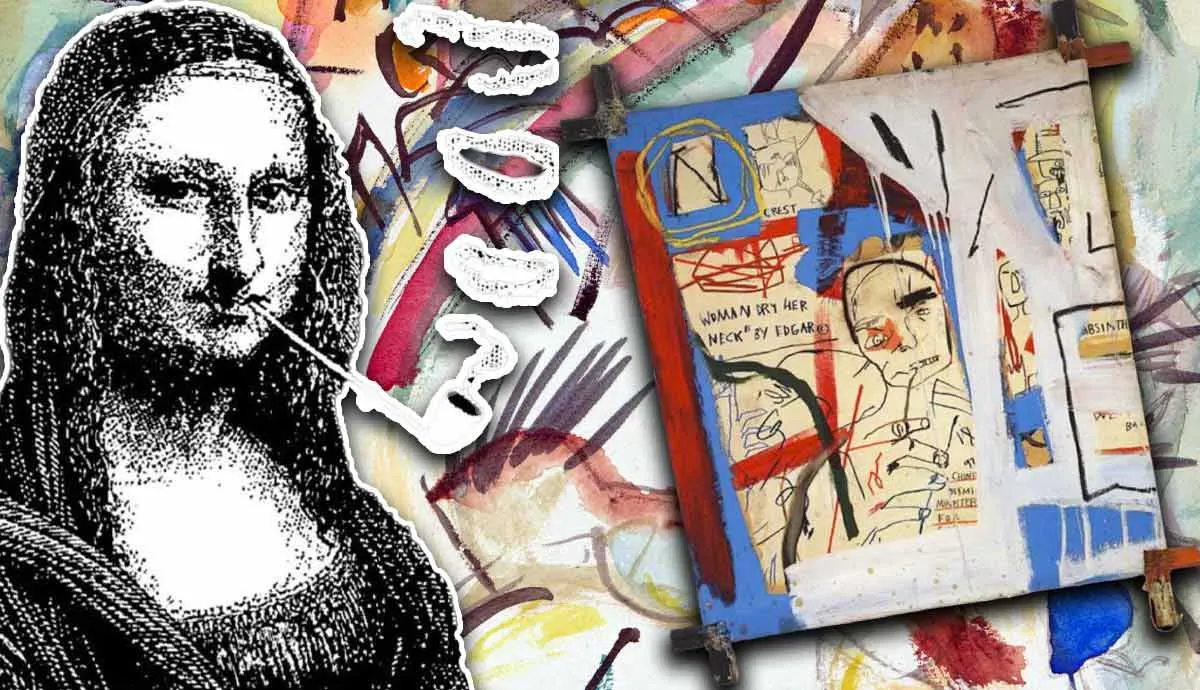从具象到超现实主义,马克·罗斯科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找到了自己的成熟风格。本文将探讨他后期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作品的意义和含义。我们也将探讨语言是否足以描述罗斯科,考虑到他对语言的怀疑和回避。最后,我们将分析几位思想家对这位神秘而具有争议性的画家的想法。
罗斯科晚期作品和对超越性的追寻
 罗斯科教堂内部,图片由艾伦·伊斯拉拍摄。来源:维基百科
罗斯科教堂内部,图片由艾伦·伊斯拉拍摄。来源:维基百科
我们该如何理解抽象艺术?抽象艺术真的有意义吗?在20世纪和21世纪,抽象艺术受到了许多赞扬和批评。一些人断言,由于抽象艺术不描绘世界,因此毫无意义。另一些人则认为抽象艺术是精英主义的,是封闭的,将它的“内容”甚至它的空虚隐藏起来,拒绝观众的审视。抽象艺术确实不像绘画那样“描绘”世界。但是,将“抽象”一词泛化只会加剧混乱。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画家被归入“抽象艺术”的类别,他们的创作意图、方法和过程都大相径庭。“抽象”这个笼统的词无法捕捉到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之间的具体性和差异。
抽象表现主义是20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艺术运动;马克·罗斯科(1903-1970)是其先驱之一。这位拉脱维亚裔画家,他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神秘作品,最终被认为是这一新运动的典范。
但即使是“抽象表现主义”这个词在描述罗斯科时也不够准确,他自己也拒绝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作品。他甚至认为“抽象”这个词具有误导性,他强调他关心的现实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因此他的艺术与自然密不可分,而不是与自然分离:“我不相信曾经存在过抽象还是具象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关于打破沉默和孤独,再次呼吸和伸展双臂的问题。”在这段引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整个艺术传统以及他对20世纪中期西方消费主义社会中个人被孤立的现象的厌恶。
 无题蚀刻作品1,巴雷特·纽曼,1968年。来源:维基百科
无题蚀刻作品1,巴雷特·纽曼,1968年。来源:维基百科
罗斯科的艺术经历了多个时期,包括表现主义对形式的扭曲、超现实主义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多形态”阶段,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形成了自己的成熟风格。对于这位艺术家来说,这一成熟阶段超越了美学,他认为美学关注艺术创新和对传统的理解以及当代发展的意识。这些作品呈现了罗斯科所说的“人类戏剧”,通常具有悲剧性的意味,因为人类必然会死亡。美学,如果理解为对艺术中美的追求,对于这些后期作品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罗斯科的目标不是美,而是精神体验的真相。
至于精英主义和封闭性的指责,这些指责不能指向罗斯科,或者至少不能指向他的创作意图。这些画作意在作为一种存在,观众要以同理心和开放的态度与之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性的。
尽管罗斯科明显地摒弃了许多绘画传统,例如创造错觉空间、描绘人物和物体以及人物与背景之间的关系,但他仍然坚持一些试图克服文化差异的传统。这些传统包括使用阴郁的深色调和黑色来象征死亡和对死亡的悲剧意识。此外,作品还展示了原始但转瞬即逝的形状或色域,这些形状或色域似乎融合和移动。罗斯科明确想要做的是创造一个空间,让人在绘画的过程中表达情感,并在观众的接受过程中引发“基本的人类情感”。
 一位男孩欣赏绿、红、蓝,马克·罗斯科,1955年,迈克尔·纽曼拍摄。来源:Flickr
一位男孩欣赏绿、红、蓝,马克·罗斯科,1955年,迈克尔·纽曼拍摄。来源:Flickr
诗人兼罗斯科的亲密好友斯坦利·库尼茨称罗斯科为“萨满”和“原始人”,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创造者。根据库尼茨的说法,罗斯科的艺术起源于魔法,本质上是道德的和精神的。虽然这些词语不是罗斯科本人的言论,但他在艺术中摒弃传统规范的行为确实表明了他渴望回归人类表达的起源,他自己也提到了精神性是他作品的首要目标。
语言的贫乏
 Cubi VI,大卫·史密斯,1963年。来源:维基百科
Cubi VI,大卫·史密斯,1963年。来源:维基百科
到20世纪中期,文学批评和艺术界出现了一种趋势,即优先考虑艺术作品本身,而不是所谓的“释义的异端”——通过描述来扭曲艺术作品,这只会造成欺骗。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国新批评,批评和分析语言不足的想法在美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大多数所谓的抽象表现主义者都认同这一观点,从画家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德·库宁到雕塑家大卫·史密斯——马克·罗斯科也持这种观点。
大多数抽象表现主义作品的观赏者都认为这些作品不可解释——包括支持者和反对者。由于解释是语言的专利,因此许多人认为艺术作品与语言是无法相比较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来写道,对音乐或艺术的文字化描述仅仅是意识形态,而真正的艺术体验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
 无题(灰底黑),马克·罗斯科,1970年。来源:古根汉姆博物馆
无题(灰底黑),马克·罗斯科,1970年。来源:古根汉姆博物馆
在罗斯科的后期作品中,语言的失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值得期待的。正如他的抽象艺术否定了或更确切地说使具象、可见世界的物体甚至他早期关注的象征和神话变得多余一样,晚期的罗斯科也唤起了语言和描述的不足,因为它们的参照物是罗斯科试图超越的物质世界中的物体和概念。将文学应用于罗斯科的视觉艺术,其自毁的项目是显而易见的。
描述,伴随着它所隐含的释义、分类、划分和比较,与罗斯科自己的项目背道而驰。他的项目追求一种普遍的崇高,摆脱了语言的束缚。正如他所说,这些画作应该被体验为纯粹的“存在”,它们应该像有机体一样活着。因此,它们不受描述的局限性要求的约束。它们也体现了对绘画的抵制,即创作一幅描绘故事、人物和物体的绘画。这样做,如果是关于故事,就会屈服于文学;如果是关于人物和物体,就会受到物质世界的限制。
 大钻石,大卫·史密斯,1952年。来源:纪念艺术馆
大钻石,大卫·史密斯,1952年。来源:纪念艺术馆
当代雕塑家大卫·史密斯与抽象表现主义者有联系,他将自己的艺术称之为“回归起源,在纯粹被语言玷污之前”。对语言能力的敌视或怀疑在许多现代主义实践者中普遍存在。罗斯科也不例外,他说解释会导致“思维和想象力的麻痹”。
如果,正如罗斯科所说,他自己的作品解释会导致麻痹,那么对于那些不仅与艺术家的创作意图脱节,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使用语言而处于必要的不理解状态的批评家或解释者来说,情况也一定是如此。
如果罗斯科的意思是,观赏者会因他的解释而陷入麻痹,而他将观赏者视为体验的伙伴,那么他的意思是,他的解释会在观赏者的脑海中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他希望与观赏者分享的自由避免了重新引入语言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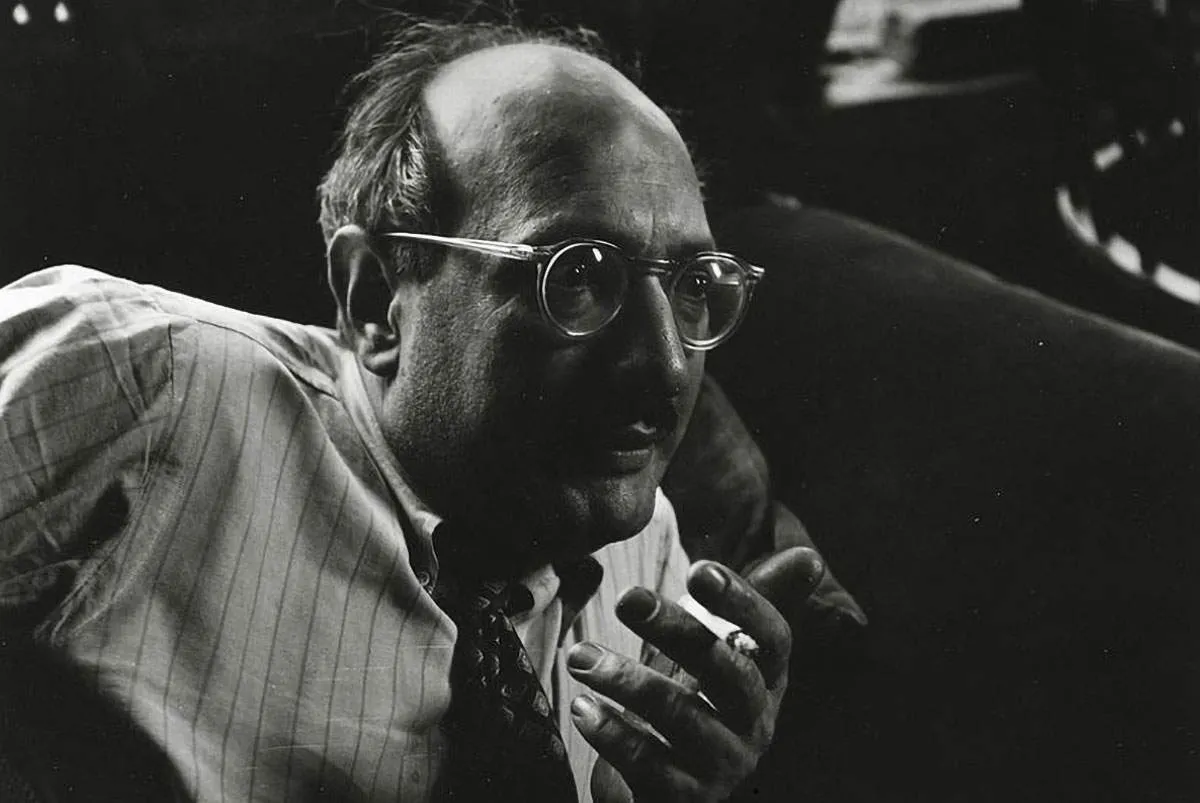 马克·罗斯科,康苏埃洛·卡纳加拍摄,约1949年。来源:维基百科
马克·罗斯科,康苏埃洛·卡纳加拍摄,约1949年。来源:维基百科
对于二战后美国许多抽象表现主义者来说,发现一种新的视觉形式的动力不仅是一种美学上的紧急情况,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紧急情况。写实主义被纳粹和苏联政权作为官方风格推崇,因此与宣传、欺骗和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艺术史学家安妮·吉布森指出,即使许多美国画家的社会现实主义也被认为带有对立的宣传意义。
罗斯科对将可分类和特定的意义强加于他的艺术,无论是出自他本人还是其他人,都感到恐惧。对他来说,观众的自主性至关重要,就像对大多数抽象表现主义者一样。然而,这种接受的自主性并非完全,因为观众的体验必然与画作的唤起有关。
语言的贫乏,正如罗斯科所断言的,也体现在他后期作品的沉默和令人沉默的“存在”中,这使得这些作品“无法书写”和“无法解释”。许多作品没有标题,或者只在标题中提到颜色,这加剧了对语言腐败的回避,甚至表明了一种色彩和形状相互作用的准音乐主题。
在这些常常是阴郁的、微妙地融合和变化的形式中,没有特定的意义可以以平淡的语言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交流。虽然没有代表特定的主题、故事、人物或物体,但画布、颜色以及我们与颜色相关的氛围是不可否认的,但又是无法定义的。
罗斯科的创作意图
 “多形态”作品:No.9,1948年,马克·罗斯科。来源:休斯顿画廊
“多形态”作品:No.9,1948年,马克·罗斯科。来源:休斯顿画廊
尽管语言存在这种缺陷,但语言仍然可以批判、分析和将艺术置于语境之中,语言是这些追求的本质。当然,语言无法表达罗斯科的作品,也无法表达任何视觉艺术作品。即使被称为“摹写”的文本,在文艺复兴时期被用来描述视觉作品,也未能达到全面性的描述,无法完全表达效果或反应,因为描述的本质就是有限的,因此也具有局限性。
对于抽象绘画而言,情况更是如此,然而,描述的工具、关系的分析以及作品之间演变的追踪可以被用来帮助我们理解。然而,罗斯科的画作本身就具有自证性;它们永远无法被详尽地描述,只能被有限地索引。
艺术家本人,尽管反对将文学和语言强加于他的作品,但他还是屈服于对作品发表了一些言论,尽管这些言论很少且言简意赅。然而,从他明确的言论中,我们知道,罗斯科感到自己被当时的美国社会所束缚,他认为这个社会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解放杠杆”。1947年,当他正处于成熟风格的边缘时,他认为艺术的使命是“超越性”体验,而这种体验却被日益消费化的社会边缘化了。他得出结论,只有在抛弃熟悉的安全感和共同体之后,他的使命才能实现。
所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都应该被抛弃,因为它们是通往真实性的障碍。他将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描述为“通往离开其发生世界的门户”,作为他创作过程和观众接受过程的前奏。
 酒红色底黑,罗斯科,1958年。来源:档案
酒红色底黑,罗斯科,1958年。来源:档案
关于画作本身,罗斯科表示:“我认为我的画作是戏剧;画作中的形状是演员”,更明确地说,他认为他的形状是独特的、有机的,“具有意志力和自我主张的热情”,不与可见世界有任何关联,可见世界是由“有限的关联组成,我们的社会正越来越多地用它来包围我们环境的方方面面”。
对罗斯科来说,存在两种悲惨的境况。第一种是现代悲剧,即超越性的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无法沟通”。第二种是存在的悲剧本质:人类的死亡。这在他的画作中既得到肯定,也得到否定,因为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他看似无限的有机空间旨在提供与能够被直觉感知的精神永恒的相遇。
后期作品旨在与这种无限的精神性进行交流,并试图为超越性体验提供一种社会方向。其目的是提供一种对内在精神的助产术,将其表现为一种笼罩着观赏者的朦胧幻影,罗斯科甚至建议观赏者与画作保持18英寸的距离。在休斯顿的罗斯科教堂,观众会被画作包围,最终达到这种身体上的包围。
尽管有些人认为罗斯科的艺术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精英主义的、难以理解的或空洞的,但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趋于普遍性。他想“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前所未有的方式解决一种永恒的、熟悉的需要”。
 马克·罗斯科的西格拉姆壁画,巴黎,让-皮埃尔·达尔贝拉拍摄,2024年。来源:维基百科
马克·罗斯科的西格拉姆壁画,巴黎,让-皮埃尔·达尔贝拉拍摄,2024年。来源:维基百科
这些画作在狭隘的意义上是抽象的,因为它们不描绘可见世界,因此不是真实的或叙事的。然而,它们意在具有意义。罗斯科试图唤起的是纯粹的存在和超越。同样,符号,即使是涉及多个事物的多义符号,也与语言息息相关。因此,罗斯科并不以暗示的方式来表达事物,而是通过形状和颜色的融合,尽可能直接地记录下他的“基本的人类情感”。
然而,这些画作不仅仅是他情感的遗物,而是从两个方面指向自身之外。第一个方面呼吁他理想的“敏感”观众的参与,观众要像对待一个人一样与作品互动:“一幅画是靠陪伴而存活的……”
画作指向自身的第二个方面是试图实现人类灵魂的炼金术。画布和颜料这些实实在在的材料,通过绘画行为,被转化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空间,这个空间拒绝被定义,反对被定义——并且几乎溢出画框。正如罗斯科的材料被转化为这种不同亮度的空间一样,艺术家和观众有限的、必死的状态也被他们对体验的真诚投入所克服——或者意在克服——。
意图与实现
 No.14,罗斯科,1960年,彼得·E.拍摄。来源:Flickr
No.14,罗斯科,1960年,彼得·E.拍摄。来源:Flickr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就成为一位重要的,如果不是最重要的,高级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家。他的影响力主导了20世纪中期的艺术批评,因此,他的思想逐渐凝固成正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无效的,而是证明了它们的影响力和洞察力。格林伯格在研究艺术,尤其是绘画时,是反意图主义者。他只关注绘画的最终成品。
然而,尽管罗斯科在很少的言论中言简意赅,但他确实提到了他表达“基本的人类情感”的意图。这样,他与格林伯格等高级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不同,格林伯格认为艺术作品只与自身有关,与意图无关。格林伯格进一步写道:“所有具有质量的绘画都要求人们去观看,而不是去阅读。”罗斯科当然也与这位批评家一样厌恶将文学强加于绘画,但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他的画作不仅要求人们观看,还要求人们与之互动或吸收观赏者,并消除格林伯格纯粹观看所隐含的距离。
同样,罗斯科与一个重要的存在主义意义地点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思想家让-保罗·萨特写道,艺术作品的意义不能仅仅用艺术家的意图来概括。事实上,萨特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在于保存观赏者的意义,因此,观赏者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存在主义坚持认为,观赏者是负责任的仲裁者,这与罗斯科的观点相关,罗斯科的画作不仅是他与崇高和超凡脱俗的对抗的记录,也是对接受性观赏者——他理想的“敏感”观赏者——的邀请,让他们参与这种体验。
 罗斯科的工作室,纽约。来源:维基百科
罗斯科的工作室,纽约。来源:维基百科
但是,虽然萨特坚持认为意义的形成是观赏者的任务,但罗斯科后期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更具互动性和更具平等性的,因为它们既是他自身体验的残留,也是对观赏者的邀请。罗斯科的观赏者既是观众,也是有回应能力的知己。
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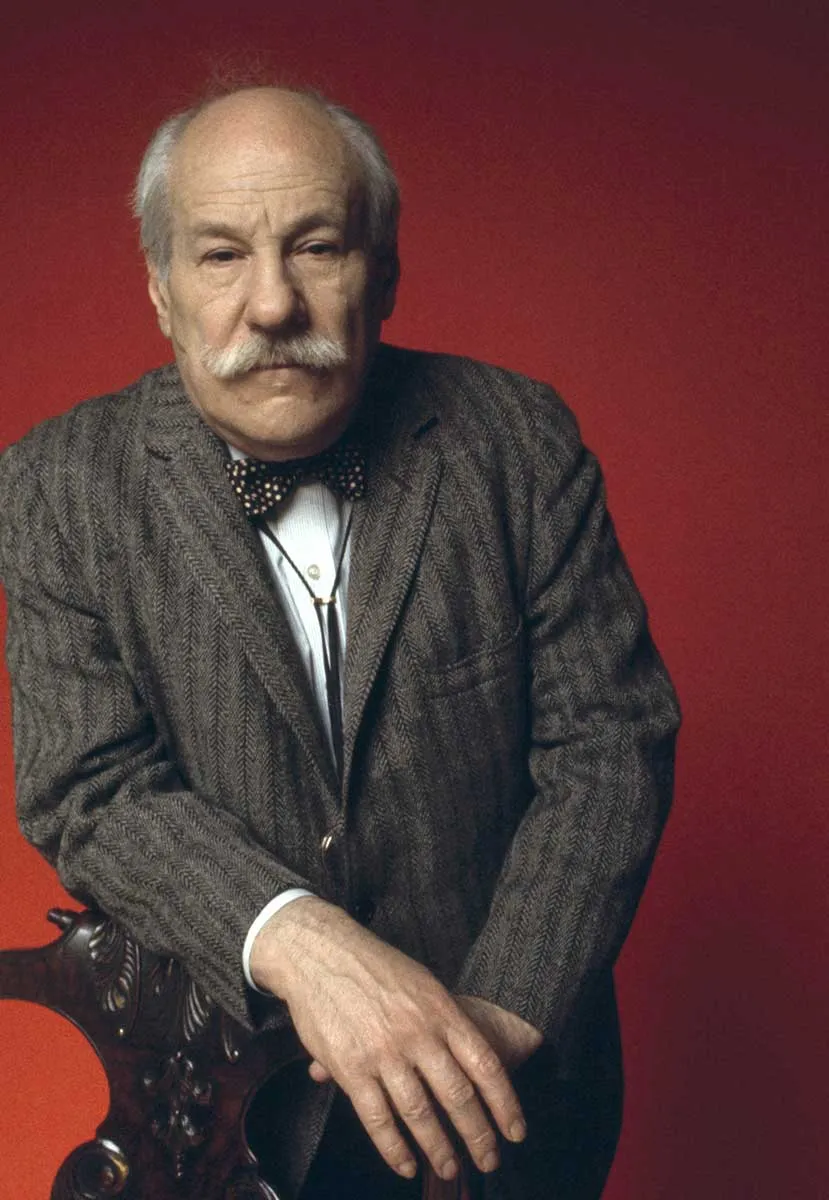 巴雷特·纽曼,1969年。来源:史密森学会
巴雷特·纽曼,1969年。来源:史密森学会
1948年,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巴雷特·纽曼指出,欧洲艺术未能实现崇高,因为它“盲目地渴望存在于感觉的现实之中”。这恰恰是罗斯科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虽然没有“感觉”的具象内容,甚至没有概念内容——因为这需要语言——但罗斯科的“色域”中蕴藏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崇高感。
艺术史学家E.H.贡布里希使用了一个恰如其分的音乐比喻来描述艺术中的表达:“我们对这种表达的反应不是针对和弦本身,而是针对在有组织的媒介中选择的和弦。” 罗斯科在作品内部和作品之间不断地、微妙地调整他的色调。他使用了鲜艳的色彩,如绿色和红色,并制造了明暗对比。后来,他更加细致地研究了深色调,展现出广泛的色调变化,以至于画框的严酷现实才为他的海洋般视野提供了突兀感。画框标志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和精神领域之间的界限,也是罗斯科希望的,艺术家与观众的敏感性之间的界限。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马克·罗斯科展,dvdbramhall拍摄。来源:Flickr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马克·罗斯科展,dvdbramhall拍摄。来源:Flickr
克劳德·塞努什基写道,罗斯科作品的观赏者必须重新构建其元素的组合:“这些关系不是在画布上,而是在观赏者的脑海中”。这与对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他们的颜色并置是通过对颜色的感知而混合的。例如,莫奈为了光影效果,几乎没有关注物体本身。
然而,对罗斯科来说,画布和颜料在他的作品中共享唯一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要通过色彩纯粹地唤起人类情感来克服。实际上,罗斯科也提到光的首要性——即他的色彩的目的是:“这不是颜色,而是光。”
 杰克逊·波洛克,1928年。来源:史密森学会
杰克逊·波洛克,1928年。来源:史密森学会
在1952年重要的文章《美国行动派画家》中,哈罗德·罗森伯格提到了行动派绘画及其表现,或者说缺乏表现的“非对象性”:“行动本身就是对象……绘画只是一个幽灵。”然而,尽管对于杰克逊·波洛克等许多“行动派画家”来说,这可能是合理的,但这与罗斯科的创作过程或意图并不相符。
对罗斯科来说,绘画行为无疑很重要,因为它试图纪念他对崇高的情感相遇。然而,他的行为与其说是终点或“对象”,不如说是开启了一种开放式的记录过程,这种过程旨在激发观赏者的交流,观赏者自身的相遇是双重的:既是对作品的体验,即从世俗中解放出感受性,又是对自身超越性体验的体验。这种后一种相遇通常是在观赏者面对罗斯科后期作品中更暗淡的作品时被激发出来的,这些作品旨在引发对死亡的悲剧意识。这些作品不仅仅是绘画行为的“幽灵”,而是纯粹的存在,期待着参与。
然而,罗森伯格与罗斯科的交汇点在于罗森伯格对现代艺术作品的看法,即“过渡到对象的另一面和意识的外部空间”,正如罗森伯格所说。罗森伯格对绘画行为的看法表现为“将心理赋予的东西转化为有意的东西,转化为‘世界’——并超越它”。当我们看待罗斯科的后期作品及其关于这些作品的论述时,这一点最为贴切。对他来说,“心理赋予的东西”就是我们可见世界中的日常生活。
 让-保罗·萨特,1967年。来源:政府印刷局
让-保罗·萨特,1967年。来源:政府印刷局
杰弗里·韦斯在罗斯科的画作中看到了源自让-保罗·萨特关于虚无的理论的“双重虚无”。根据萨特的观点,双重缺席在于,缺席的人物被体验为存在,“或者是对虚无的理解,而充实被体验为基础。”韦斯将这一点应用于罗斯科,指出罗斯科对“人物”和“背景”,或者说中心和边缘的操控。但这至少破坏了罗斯科的意图,可能也破坏了他画作的视觉证据。人物与背景关系与罗斯科的画作无关。不仅人物缺席,人物与背景的关系也缺席。然而,从概念上讲,整幅画作可以被看作是观赏者精神体验的“背景”,也可以被看作是引发这种体验的“人物”,或者说是准主观存在。
将萨特的虚无感应用于罗斯科的艺术似乎是一种牵强的、武断的行为。虽然罗斯科确实放弃了物质世界,从而放弃了具象,但萨特的虚无意味着对存在的否定。罗斯科并没有否定存在,他只是否定了存在的物质方面,以唤起不受人物及其所包含的物体束缚的纯粹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更像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萨特建立了一个过程,通过否定存在来产生虚无,但罗斯科否定了存在的物质方面,以产生与精神上真实但无形的某种东西的交流。更广泛地说,罗斯科和萨特都对真实性有着强烈的关注。
 罗斯科教堂,休斯顿,德克萨斯州,迈克·林克斯维尔拍摄。来源:Flickr
罗斯科教堂,休斯顿,德克萨斯州,迈克·林克斯维尔拍摄。来源:Flickr
对于莱奥·贝尔萨尼和尤利斯·杜图瓦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罗斯科“开始颠覆形式的可读性”,这项事业最终在罗斯科教堂中达到顶峰。这种观点是无可争议的。贝尔萨尼和杜图瓦认为,由此产生的可见性不再必要,是一种盲目。可见性不再必要是可以争论的,但与其说这会导致盲目,不如说可见性被对视觉的追求所取代,这种追求是由画家看似无限的无形所传达的,这种无形代表着永恒和崇高。
根据贝尔萨尼和杜图瓦的说法,20世纪50年代的罗斯科是“对观看时刻的回归”,并重新唤起了“存在可能不会发生”的可能性。他们将罗斯科称为“倒退”。但存在确实存在于这些画作中,罗斯科认为这些画作是由“有机的”和“有意志力的”形状构成的。这些形状在观看过程中会移动和生长。贝尔萨尼和杜图瓦似乎认为存在是指对具象形式的描绘——这是一个无法适用于艺术家目标的传统概念。与其说是一种“倒退”的回归到观看的时刻,不如说在罗斯科的作品中,存在一种抛弃观看的意味——寻找(一种形式,一个人物)——而是一种超越这些的观看。寻找物体意味着眼睛的孤立体验,而在罗斯科的作品中,目标是激发一种更整体的体验,即画作(不)具有的有机存在。
参考文献
查尔斯·哈里森和保罗·伍德(编辑),《艺术理论 190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