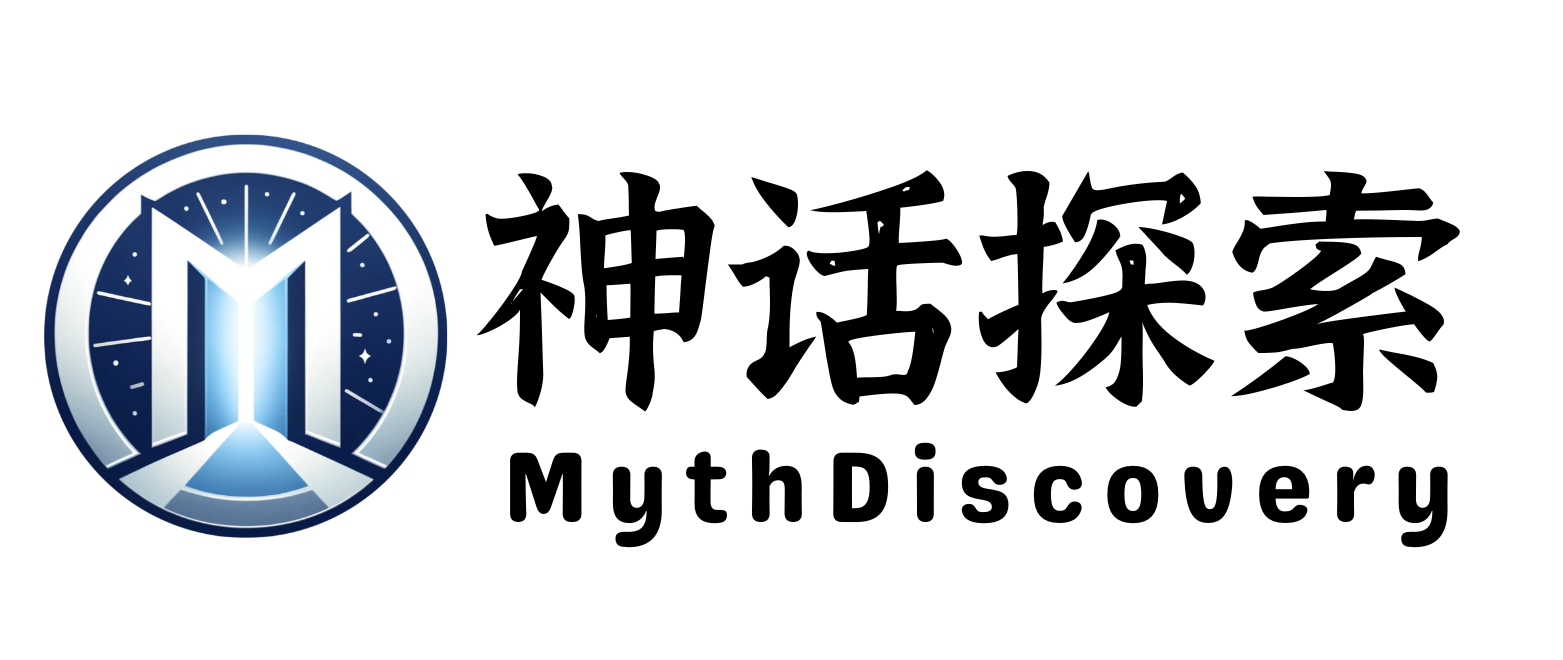“`html

1941年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虽然对欧洲人口结构的影响不及纳粹德国,但其对塞尔维亚人、罗姆人及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残酷至极,其历史和记忆也为我们理解种族灭绝、恐怖统治和纪念机制提供了深刻教训。本文将揭示鲜为人知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及其种族灭绝行动,从其独特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入手,探讨其种族灭绝的实施,并分析围绕种族灭绝记忆的一些问题。
矛盾的实践: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主义者对塞尔维亚人怀有特殊的仇恨,视其为天主教的叛徒。这使得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及其代表政党——乌斯塔沙——有别于其他轴心国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此外,乌斯塔沙领导人兼“克罗地亚独立国”独裁者安特·帕维利奇认为,塞尔维亚人的存在威胁着克罗地亚文化,他将塞尔维亚人视为“斯拉夫宣传”的产物,并认为他们几个世纪以来都在试图“掌控”克罗地亚社会。
在为其种族灭绝行动定义意识形态时,克罗地亚独立国(NDH)的部长们不得不走钢丝。历史上也不存在纯粹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犹太人和罗姆人几个世纪以来互相融合。定义纯粹克罗地亚人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极端的罗马天主教原教旨主义,以及声称克罗地亚人起源于日耳曼民族。
这种种族纯洁的愿景包含着一个奇怪的矛盾;它包含了波斯尼亚人,因为帕维利奇认为他们只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为了保护克罗地亚文化而改信伊斯兰教的克罗地亚人 (Adriano, Cingolani, and Vargiu, 2018, p. 191)。
乌斯塔沙招募克罗地亚天主教神父监督改宗、逮捕甚至屠杀。在NDH的鼓励下,多年来与犹太人、罗姆人和塞尔维亚人共同生活的神父们背叛了他们的邻居和朋友。
真相即将揭露

1941年4月30日,NDH剥夺了所有东正教徒的公民身份,禁止使用西里尔字母,关闭所有东正教机构,并禁止使用“塞尔维亚东正教信仰”一词。任何不能证明拥有“足够雅利安克罗地亚血统”的人必须佩戴臂章。
乌斯塔沙政权在其部长宣布帕维利奇政权打算效仿纳粹德国的政策时,更加明确地表明了其对犹太人的态度。该政权要求他们佩戴带有克罗地亚字母“ž”(代表židov,即犹太人)的黄色圆盘 (McCormick, 72)。
为了恐吓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罗姆人改宗,乌斯塔沙士兵袭击了利卡的民宅 (Glenny, 486-9)。这些暴徒在夜间洗劫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家园,强迫家庭和个人在几分钟内收拾好他们的财物,然后将他们拖到灭绝营,第一个灭绝营科普里夫尼察于1941年5月启用。到1941年5月底,科普里夫尼察关押着3000名塞尔维亚囚犯。
六月,帕维利奇和布达克下令建立三个新的集中营——帕格岛上的两个营地,斯拉纳男子营和梅塔尼亚女子营,以及位于维莱比特山脉山区城市亚多夫诺的一个营地。
1941年8月,意大利士兵接管帕格岛时,发现了791具尸体,一名军官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几乎所有男尸的上下肢都被捆绑了……大多数尸体的胸部、背部和颈部都有刀造成的致命伤口。在所有受害者都死之前,这些坑就被草率地用泥土和石头掩埋了,大多数尸体的悲惨表情证明了这一点”(Adriano, Cingolani, and Vargiu, 192)。
然而,与雅塞诺瓦茨相比,帕格营地只是暴力浪潮中的一小部分。
雅塞诺瓦茨:持续的信息战的象征

关于雅塞诺瓦茨集中营及其相关的种族灭绝事件的事实至今仍在激烈争论中,塞尔维亚政客夸大其词,而克罗地亚政客,例如前总统弗兰乔·图季曼本人则试图淡化其严重性。然而,驳斥任何一方的说法的问题在于,几乎没有客观的数据能够明确界定1941年至1945年国家批准的受害者人数。
雅塞诺瓦茨于1941年8月启用,由位于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边界上的五个营地组成。雅塞诺瓦茨一号和二号于1941年11月关闭,因为乌斯塔沙处决了所有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和罗姆人囚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人手同时运营所有五个营地。雅塞诺瓦茨三号关押巴尔干犹太人、罗姆人和辛提人,然后将他们送往奥斯维辛灭绝。雅塞诺瓦茨四号和五号主要关押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政治异见者。
雅塞诺瓦茨最初占地60平方英里。到1945年,它已扩大到130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亚特兰大或拉斯维加斯的大小。
1941年8月,装满饥饿疲惫的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罗姆人的破旧牲畜车驶向雅塞诺瓦茨。

囚犯们到达了一个设计容纳7000人的营地,但它从未达到这个容量,因为人们死得太快了。如果他们能通过大门,他们就会发现粪坑溢出的恶臭、未洗的尸体、血迹和腐败的气息压倒了所有下车的囚犯。
偶尔,烟味会从烟囱里飘出来,灰烬会落在铁轨和营房旁的泥土上。这些灰烬来自营地焚尸炉,乌斯塔沙暴徒将活人塞进营地砖厂的熔炉里。一旦经过处理和判决,由专横且经常嗜血的营地工作人员判决,就会得到一个碗和薄衣服;也就是说,如果还适合工作的话。
食物通常是用卷心菜叶调味的热水。囚犯吃草和树叶,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吃死动物的尸体,绝望地抓住任何能找到的可食用东西以求生存。警卫禁止塞尔维亚囚犯饮用任何饮用水。他们必须从萨瓦河饮水,萨瓦河曾经碧绿清澈的水中含有粪坑废物和腐烂的尸体。

工作本身经常导致囚犯死亡,因为建筑、农业、砖瓦和铁匠工作经常使这些疲惫不堪的人面临危险情况,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囚犯被烧死、从建筑物上掉下来,或在重物下倒塌。
到1941年10月,饥饿开始导致囚犯死亡。日复一日,他们努力寻找食物,有些人甚至去粪坑里寻找未消化的豆子或卷心菜叶。
营房也不适合生存。它们是仓促建造的,墙壁和屋顶上有许多缝隙,冬天雨水和雪会渗透进来。一系列痛苦的、长期存在的疾病——伤寒、斑疹伤寒、疟疾、白喉,甚至流感——杀死了数千名囚犯,他们的尸体被遗弃腐烂,恶化了幸存囚犯的生存条件。
共有八个营房;囚犯住在其中的六个营房里。最后两个是“医务室”和“诊所”。如果一个人被送去那里,很可能就意味着没有人会再看到他们活着了。

这两个营房的警卫和工作人员要么等待囚犯死亡,要么从1942年开始,将一批垂死的囚犯带到砖窑,在那里将人们活活烧死,为更多囚犯腾出空间。
这并不是乌斯塔沙为雅塞诺瓦茨腾出更多囚犯空间的唯一方式。在附近的格拉迪纳地区,乌斯塔沙专门圈出一块土地用于囚犯“处决”。乌斯塔沙将罗姆人和辛提囚犯集中起来,并将他们押送到这个处决场进行屠杀。
1942年8月之后,看到纳粹德国对处决犹太人的狂热,乌斯塔沙决定开始将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仅仅在一个雅塞诺瓦茨营地,乌斯塔沙就在一年内消灭了8000到25000名犹太人,当时约占克罗地亚犹太人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余的将由纳粹德国负责。乌斯塔沙警卫然后可以专注于“大克罗地亚”的罗姆人、辛提人,最重要的是塞尔维亚人。
他们一直这样做直到1945年4月。在此过程中,这个营地可能杀害了大约10万人:近5万塞尔维亚人,约2万罗姆人和辛提人,1.3万犹太人,4000克罗地亚人和1000波斯尼亚人。
仔细观察人口统计数据,事实变得更加令人不安。在这个集中营中,估计有10万受害者中,有超过5万是妇女和儿童。在营地运营期间,雅塞诺瓦茨共有50多个集体墓地,其中许多直到几十年后才被挖掘或发现。
后果

在整个被占领的“大克罗地亚”,共有20万至50万塞尔维亚人、罗姆人、辛提人、犹太人和政治异见者被杀害,其中超过一半是塞尔维亚人,他们被认为是乌斯塔沙地区人口最多的目标群体。随着1945年夏季初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的终结,种族灭绝也随之结束。随着共产党游击队的壮大,帕维利奇将他的乌斯塔沙投入了两件事:对抗游击队和逃离巴尔干半岛。
在北部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上,在同情乌斯塔沙的神父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条逃亡路线。帕维利奇和其他高级官员逃往奥地利,然后逃往罗马。从那里,许多人逃往阿根廷,逃脱了他们对无数其他人施加的惩罚。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从乌斯塔沙的灰烬中崛起。南斯拉夫人民受到了创伤,难以相互信任。铁托政府表面上允许每个民族认同其身份和使用其语言。但现实却更为复杂。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拉维采纪念馆等纪念碑如今已杂草丛生,常常让不知情的人对其用途产生疑问。这座纪念碑上的一块牌匾,摘录了伊万·戈兰·科瓦奇奇的《雅玛》节选,揭示了其用途:纪念克罗地亚独立国制造的大屠杀。
与战后时期的德国类似,人们建造了为受害者服务的纪念碑。然而,在铁托的南斯拉夫,乌斯塔沙很少在学校或机构中被提及。因此,由于缺乏正式的、积极的与历史和解的努力,该地区的一些社区继承了希望报仇雪恨的愿望,而另一些社区则担心再次发生种族灭绝。
因此,塞尔维亚人在20世纪90年代经常提及雅塞诺瓦茨集中营。当克罗地亚宣布独立时,甚至在其国旗上使用与乌斯塔沙相同的纹章,这促使害怕和希望复仇的社区拿起武器对抗新独立的克罗地亚政府——这表明这场种族灭绝的长期紧张局势和历史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