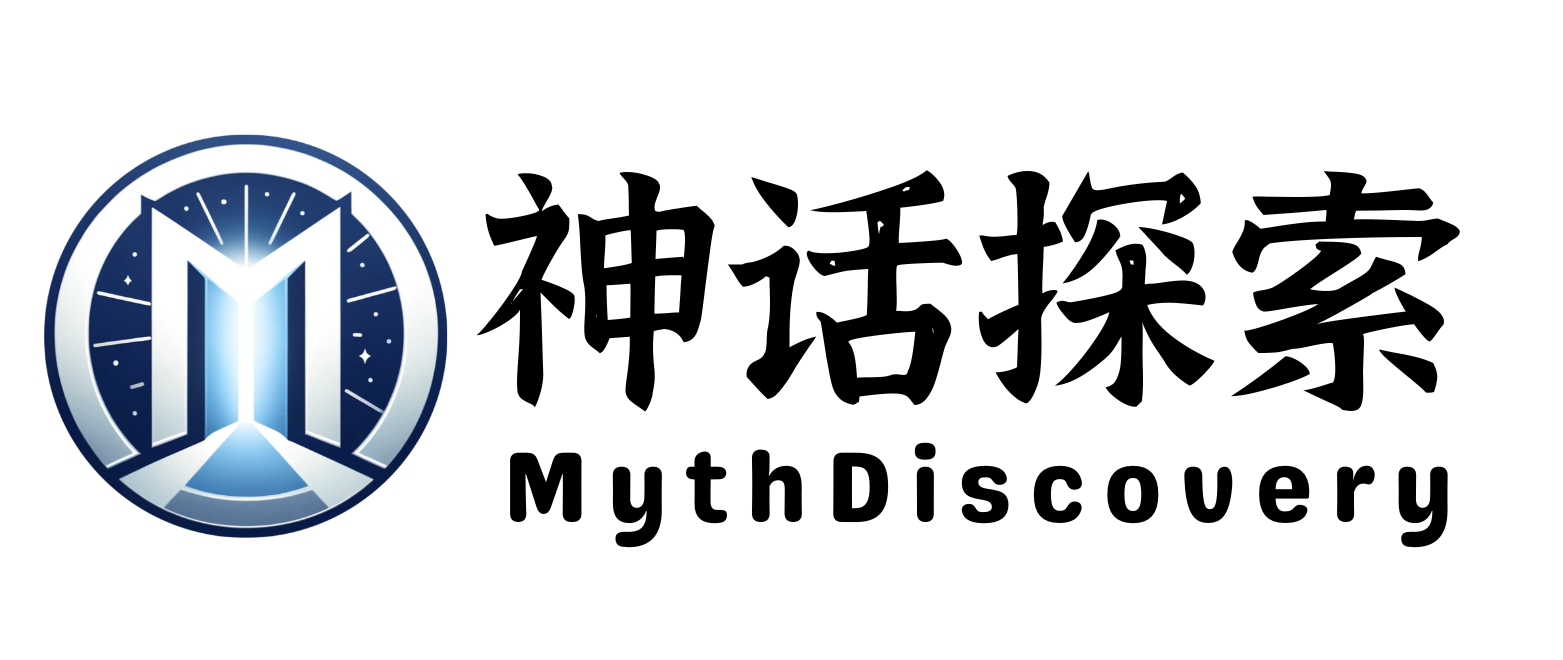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如今却被认为已死,主要被用作一种反面论证、一种漫画和一个稻草人,很容易被驳倒并用于支撑其他观点。尽管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遭到嘲笑,但他们的思想和影响仍然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现代的科学哲学中,并且帮助塑造了逻辑和人文等领域。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它的讣告是否写得太草率了?
实证主义:通往现代科学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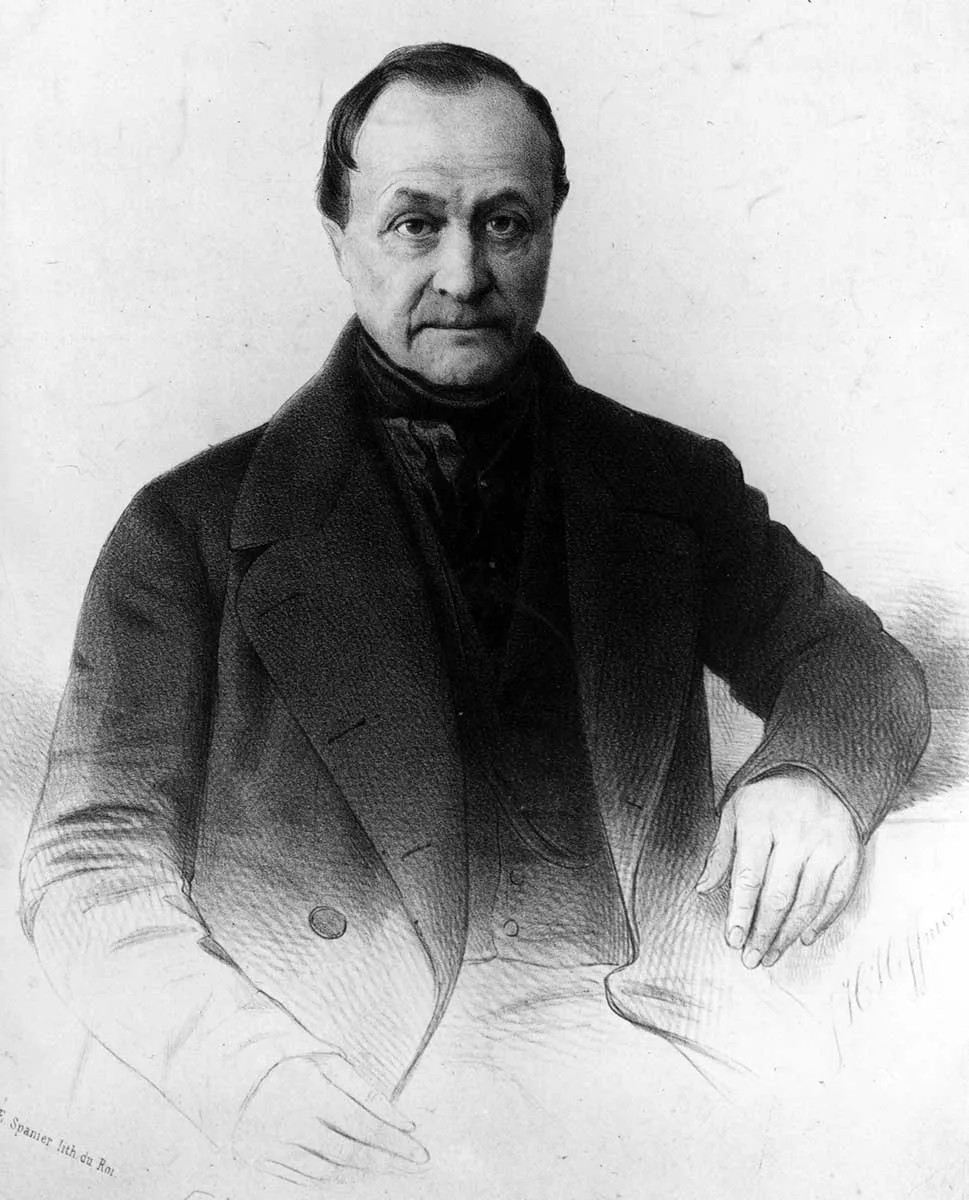
实证主义最初由奥古斯特·孔德创立,他深受其老师圣西门的启发,实质上是通往现代科学哲学的第一步——然而,实证主义本身当时更像是一个为了改善社会而发起的运动。
孔德的思想可以在他的一句名言中体现:“爱作为原则,秩序作为基础;进步作为目标”(孔德,《实证政治体系》,1841-45,第19页)。他试图通过历史视角来创造一种理性思考的方法,并希望加速科学从之前部分受宗教支配向完全世俗化的转变。
孔德认为科学(用孔德的话来说就是“实证”)知识是社会知识的最终演进,它建立在神学和随后的形而上学知识之上。这就是为什么孔德也想要抛弃形而上学知识,因为他认为形而上学知识是启蒙运动及其理性主义的残余,阻碍了进步。
孔德相信科学存在一个等级制度,其中较不复杂、更一般的科学,例如物理学,处于顶端,而更复杂、更具体、更依赖于其他科学的科学,例如社会学,处于底部。这种等级制度使得位于顶部的科学更加决定性。
休谟对实证主义发展的影响

实证主义哲学深受休谟的经验主义和科学反实在论的影响。关于事实问题的知识只能基于正面的观察数据或逻辑证明。理论实体和规律,例如电子和引力,是不可观察的,仅仅是预测工具。
这种立场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一种反形而上学的观点。休谟写道:
“如果我们拿起任何一本书,比如神学或学校形而上学,让我们问问自己,它是否包含关于数量或数字的抽象推理?不。它是否包含关于事实和存在的经验推理?不。那就把它扔进火里吧:因为它只能包含诡辩和幻觉。”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1748,第12节,第3部分
逻辑实证主义:语言与逻辑

科学哲学中的下一个重大运动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名义下形成的,正如实践者自己所称的那样——因为他们不想与之前的运动及其带来的包袱直接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们最初的哲学信念是其的直接延续,并建立在后来实证主义者,如马赫和阿维纳留斯的成果之上。
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分为两派:维也纳学派和柏林社团。维也纳学派主要由鲁道夫·卡尔纳普、奥托·奈拉特、汉斯·哈恩和莫里茨·施利克领导,而柏林社团则由汉斯·赖兴巴赫领导。
逻辑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相似,它更像是一个运动,而不是一个哲学学派,他们甚至在试图改善社会方面有着明确的共性。他们想要统一科学,他们通过统一科学语言来寻求这一目标,并试图消除开始渗透到社会中的不可证伪的论断——甚至在科学领域。
实证主义运动后来被其继任者掩盖了;人们通常会误解实证主义,将其等同于后来的运动。
通过语言统一科学

逻辑实证主义通过使用语言、意义和逻辑的哲学来实现其目标,从而将其与之前的运动区分开来。
他们看到了逻辑和数学作为一种通用语言的可能性,这种语言可以用来统一科学。通过用这种精确的语言来表达理论和规律,他们希望消除歧义,并确保科学学科和哲学之间的严谨性。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以及罗素在逻辑方面的广泛工作,激发了这种想法。总而言之,这暗示了语言的结构反映了世界的逻辑结构,而数学可以归结为逻辑。数学真理可以用逻辑来解释,而不是形而上学。这将在数学真理和世界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对经验主义者来说非常吸引人。
逻辑实证主义延续了罗素提出的工作,建立在休谟在分析-综合区分论断真理方面的成果之上,修改它,以便论断的真理可以通过其自身含义和/或逻辑结构,或者通过经验观察来确定。
逻辑实证主义者希望逻辑能够使科学和哲学语言变得明确和普遍。
需要一种方法来区分科学和哲学中的有意义和无意义的陈述。这是通过维特根斯坦首次提出的证伪原则来尝试的。这一原则认为,只有可以被证伪为分析的或合成的才是有科学意义的。这使得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陈述在科学上毫无意义。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在此情况下,有意义意味着具有真值。在科学真理方面无意义的东西,在总体上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无意义的。
质疑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

逻辑实证主义最初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运动,旨在建立一种基于逻辑和数学的通用科学语言,但它很快就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威胁着要破坏其基础。
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和塔尔斯基的不可定义定理揭示了形式语言的局限性,即使是基于逻辑或数学的形式语言。这些定理让人对创造一个完整且一致的系统来表达所有科学真理产生了怀疑。
证伪主义的概念,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也面临着审查。证伪悖论突出了证伪主义本身的自相矛盾的性质,因为它的标准无法证伪它本身。如果一个有意义的句子必须通过分析或观察来证伪,那么证伪原则本身就超出了这个定义。
此外,奎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提出了质疑,他质疑了分析真理和综合真理之间的基本区别以及分析性的必要性。奎因提出了一个更为整体的科学观,在这个观点中,分析真理与经验信念交织在一起,无法孤立出来。他还反对将意义简化为经验,认为意义源于信念和概念的相互交织的网络。
这些挑战共同削弱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并导致了它作为主导哲学运动的衰落。虽然它最初的雄心壮志大胆而充满希望,但形式语言的局限性、证伪主义的自相矛盾的性质以及对分析性的批判,构成了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
卡尔纳普的回应

事实上,这些发现将导致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凝聚力的运动的消亡,尽管它不是一个学派,但这些思想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
逻辑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是这一发展的关键人物。他通过修改分析标准,将注意力从句法转移到语义上来解决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所揭示的局限性。通过引入真理和意义等概念,卡尔纳普试图规避形式语言的局限性。
卡尔纳普的容忍原则为证伪问题提供了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他抛弃了单一、普遍的科学语言的想法,提出了一种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不同的科学探究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和逻辑,只要它们遵循科学方法。这种灵活的方法允许科学表达的多样性,同时保持经验探究的严谨性。
卡尔纳普还开始探索确认主义作为严格证伪主义的替代方案,认识到科学主张往往依赖于概率证据,而不是绝对证明。他还摆脱了定义上的还原性,承认科学概念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
虽然卡尔纳普的工作保留了对经验主义的强烈实证主义强调,但他对语言哲学的参与使他从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始框架中显著偏离。然而,这种转变不应被视为失败。相反,它反映了哲学探究的动态性质以及适应新挑战和发现的必要性。
正如卡尔纳普所证明的那样,逻辑实证主义从来都不是一个僵化的学派,而是一群有着共同目标和基础的思想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务实的做法体现了这一运动的探究精神,而他的工作最终为科学哲学的下一阶段铺平了道路。
后实证主义:吸取批评

卡尔纳普的进步是科学哲学转变的一条线索,这种转变是建立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后实证主义,顾名思义,是对两种实证主义核心原则的演进。这种演进是建立在批评之上的,但核心原则和理想基本保持不变。所做的仅仅是放松了约束,并认识到了理性、经验主义的局限性,以及主观性和谬误如何影响科学。
这些认识来自多个来源,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避免。最突出的例子是库恩及其革命性的科学哲学,它在多个方面给实证主义带来了问题。他关于理论加载观察的想法意味着,一个人所持有的潜在理论将影响他们所观察到的东西。这使得经验主义中的纯粹客观观察标准变得不可能,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通用科学语言。
这使得后实证主义采取了一种更加多元化的科学立场,接受近似真理或真理通过理论进行调控。它还允许一种更加科学的实在论方法,通过放松经验约束,允许接受不可观察的实体和过程的现实性。
死亡还是漫画的死亡?

对逻辑实证主义命运的看法反映在约翰·帕斯莫的一句话中:“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已经死了,或者说像一个哲学运动所能达到的那样死了。”(帕斯莫,1967,第57页)。事实上,作为一种运动,它已经消亡了,但它的思想却延续了下来。这往往被人忽视。
也许是不公正地,逻辑实证主义主要作为哲学的漫画而存在,一种通过将其对形而上学的意义归结为科学的科学主义。然而,他们并没有否定哲学,也没有认为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毫无用处——只是缺乏真值。
另一个漫画是,实证主义者拒绝承认任何不可观察的东西,但承认其现实和科学现实之间存在差异。虽然他们对不可观察的东西持怀疑态度,但他们主要不想为其赋予真值。相反,他们将不可观察的实体和过程视为预测工具,这种观点与现代科学反实在论并不遥远。
A. J. 艾尔的影響

逻辑实证主义的漫画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将该运动解释为由 A. J. 艾尔关于维也纳学派的二手写作所塑造。艾尔是英语世界的第一个连贯的翻译者,比卡尔纳普更容易理解。这可以在英语世界对证伪标准的关注中得到体现,证伪标准并非旨在成为对世界的提议,这意味着它不会破坏自身和原则,而卡尔纳普等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而艾尔的观点则将其塑造成该运动的形状。
最终,并非实证主义的观念消亡了,而是科学作为一种完全理性的、经验的企业的简单化观点消亡了。与逻辑实证主义希望统一语言以及使用语言哲学来分配真理的目标一起消亡。考虑到实证主义者崇高而值得赞扬的目标,嘲笑他们可能是不公平的。通过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该运动的特点在现代科学哲学中得以保留。
参考文献
Friedman, M. (1999). Reconsidering logical positivism (1. publ). Cambridge Univ. Press.
Passmore, J. A. (1967). Logical Positivism. In P. Edwards (Ed.),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pp. 52–57). Macmillan.
Quine, W. V. O. (1951).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Philosophical Review, 60(1), 20–43. https://doi.org/10.2307/2266637
Verhaegh, S. (2024). Logical Positivism: The History of a “Caricature.” Isis, 115(1), 46–64. https://doi.org/10.1086/728796